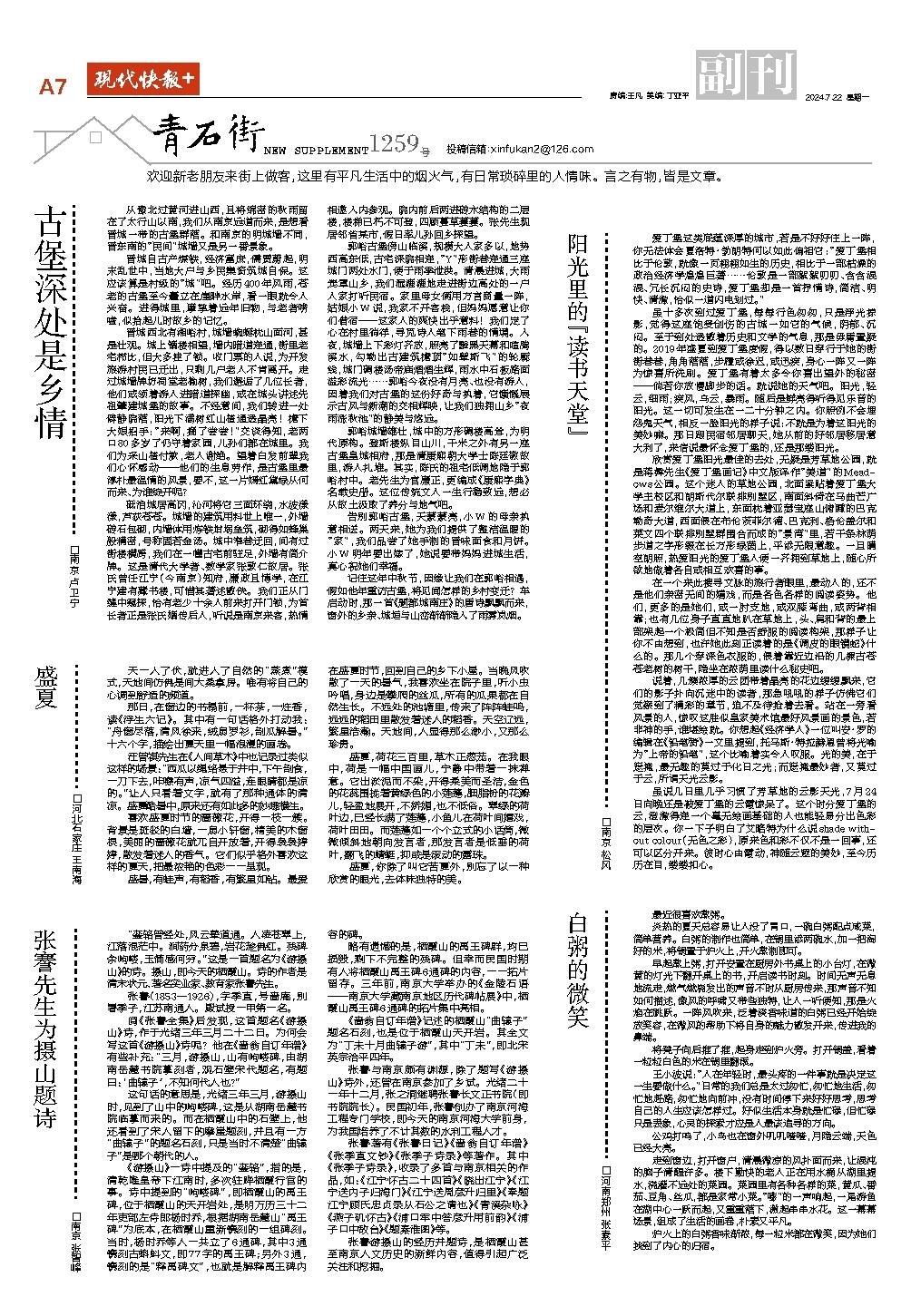□南京 卢卫宁
从豫北过黄河进山西,且将绵密的秋雨留在了太行山以南,我们从南京远道而来,是想看晋城一带的古堡群落。和南京的明城墙不同,晋东南的“民间”城墙又是另一番景象。
晋城自古产煤铁,经济富庶,儒贾蔚起,明末乱世中,当地大户与乡民集资筑城自保。这应该算是村级的“城”吧。经历400年风雨,苍老的古堡至今矗立在崖畔水岸,看一眼就令人兴奋。进得城里,摩挲着远年旧物,与老者唠嗑,似拾起儿时故乡的记忆。
晋城西北有湘峪村,城墙蜿蜒枕山面河,甚是壮观。城上镝楼相望,墙内暗道连通,街里老宅栉比,但大多挂了锁。收门票的人说,为开发旅游村民已迁出,只剩几户老人不肯离开。走过城墙牌坊祠堂老榆树,我们邂逅了几位长者,他们或领着游人进暗道探幽,或在城头讲述先祖肇建城堡的故事。不经意间,我们转进一处僻静院落,阳光下满树红山楂通透晶亮!檐下大娘招手:“来啊,摘了尝尝!”交谈得知,老两口80多岁了仍守着家园,儿孙们都在城里。我们为采山楂付款,老人谢绝。望着白发前辈我们心怀感动——他们的生息劳作,是古堡里最淳朴最温情的风景,要不,这一片嫣红黛绿从何而来、为谁绽开呢?
砥洎城居高冈,沁河将它三面环绕,水波漾漾,芦荻苍苍。城墙的建筑用料世上唯一,外墙砖石包砌,内墙体用炼铁坩埚垒筑,砌得如蜂巢般精密,号称固若金汤。城中窄巷迂回,间有过街楼横跨,我们在一幢古宅前驻足,外墙有简介牌。这是清代大学者、数学家张敦仁故居。张氏曾任江宁(今南京)知府,廉政且博学,在江宁建有藏书楼,可惜其著述散佚。我们正从门缝中窥探,恰有老少十余人前来打开门锁,为首长者正是张氏嫡传后人,听说是南京来客,热情相邀入内参观。院内前后两进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楼梯已朽不可登,四顾蔓草萋萋。张先生现居邻省某市,假日率儿孙回乡探望。
郭峪古堡傍山临溪,规模大人家多以,地势西高东低,古宅深院相连,“Y”形街巷连通三座城门两处水门,便于雨季泄洪。清晨进城,大雨笼罩山乡,我们湿漉漉地走进街边高处的一户人家打听民宿。家里母女俩用方言商量一阵,姑娘小W说,我家不开客栈,但妈妈愿意让你们借宿——这家人的爽快出乎意料!我们定了心在村里徜徉,寻觅诗人笔下雨巷的情境。入夜,城墙上下彩灯齐放,照亮了黢黑天幕和喧腾溪水,勾勒出古建筑檐顶“如翚斯飞”的轮廓线,城门碉楼汤帝庙熠熠生辉,雨水中石板路面溢彩流光……郭峪今夜没有月亮、也没有游人,因着我们对古堡的这份好奇与执着,它慷慨展示古风与新潮的交相辉映,让我们独拥山乡“夜雨涨秋池”的静美与悠远。
郭峪城墙雄壮,城中的方形碉楼高耸,为明代原构。登斯楼纵目山川,千米之外有另一座古堡皇城相府,那是清康熙朝大学士陈廷敬故里,游人扎堆。其实,陈氏的祖宅低调地隐于郭峪村中。老先生为官廉正,更编成《康熙字典》名载史册。这位传统文人一生行稳致远,想必从故土汲取了养分与地气吧。
告别郭峪古堡,天蒙蒙亮,小W的母亲执意相送。两天来,她为我们提供了整洁温暖的“家”,我们品尝了她手制的晋味面食和月饼。小W明年要出嫁了,她说要带妈妈进城生活,真心祝她们幸福。
记住这年中秋节,因缘让我们在郭峪相遇,假如他年重访古堡,将见闻怎样的乡村变迁?车启动时,那一首《题都城南庄》的唐诗飘飘而来,窗外的乡亲、城垣与山峦渐渐隐入了雨雾岚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