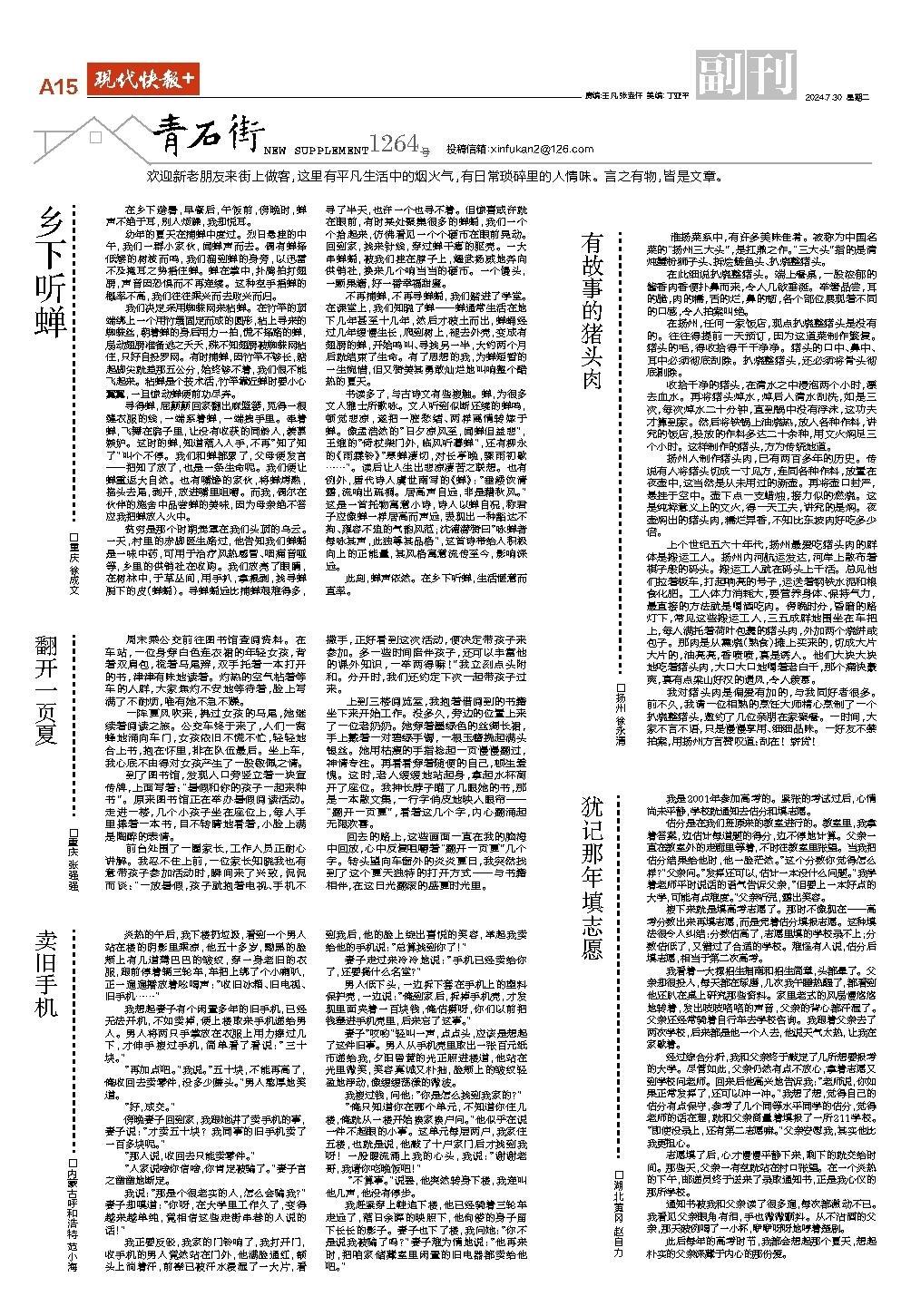□重庆 徐成文
在乡下避暑,早餐后,午饭前,傍晚时,蝉声不绝于耳,别人烦躁,我却悦耳。
幼年的夏天在捕蝉中度过。烈日悬挂的中午,我们一群小家伙,闻蝉声而去。偶有蝉择低矮的树枝而鸣,我们溜到蝉的身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捂住蝉。蝉在掌中,扑腾拍打翅膀,声音因恐惧而不再连续。这种空手捂蝉的概率不高,我们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我们决定采用蜘蛛网来粘蝉。在竹竿的顶端绑上一个用竹篾固定而成的圆形,粘上寻来的蜘蛛丝,朝着蝉的身后用力一拍,慌不择路的蝉,扇动翅膀准备逃之夭夭,殊不知翅膀被蜘蛛网粘住,只好自投罗网。有时捕蝉,因竹竿不够长,踮起脚尖就差那五公分,始终够不着,我们恨不能飞起来。粘蝉是个技术活,竹竿靠近蝉时要小心翼翼,一旦惊动蝉便前功尽弃。
寻得蝉,屁颠颠回家翻出麻篮篓,觅得一根缝衣服的线,一端系着蝉,一端拽手里。牵着蝉,飞舞在院子里,让没有收获的同龄人,羡慕嫉妒。这时的蝉,知道落入人手,不再“知了知了”叫个不停。我们和蝉都累了,父母便发言——把知了放了,也是一条生命呢。我们便让蝉重返大自然。也有嘴馋的家伙,将蝉烤熟,掐头去尾,剥开,放进嘴里咀嚼。而我,偶尔在伙伴的施舍中品尝蝉的美味,因为母亲绝不答应我把蝉放入火中。
贫穷是那个时期笼罩在我们头顶的乌云。一天,村里的赤脚医生路过,他告知我们蝉蜕是一味中药,可用于治疗风热感冒、咽痛音哑等,乡里的供销社在收购。我们放亮了眼睛,在树林中,于草丛间,用手扒,拿棍剥,找寻蝉脱下的皮(蝉蜕)。寻蝉蜕远比捕蝉艰难得多,寻了半天,也许一个也寻不着。但惊喜或许就在眼前,有时某处聚集很多的蝉蜕,我们一个个拾起来,仿佛看见一个个硬币在眼前晃动。回到家,找来针线,穿过蝉干瘪的躯壳。一大串蝉蜕,被我们挂在脖子上,耀武扬威地奔向供销社,换来几个响当当的硬币。一个馒头,一颗果糖,好一番幸福甜蜜。
不再捕蝉,不再寻蝉蜕,我们踏进了学堂。在课堂上,我们知晓了蝉——蝉通常生活在地下几年甚至十几年,然后才破土而出,蝉蛹经过几年缓慢生长,爬到树上,褪去外壳,变成有翅膀的蝉,开始鸣叫、寻找另一半,大约两个月后就结束了生命。有了思想的我,为蝉短暂的一生惋惜,但又赞美其勇敢灿烂地叫响整个酷热的夏天。
书读多了,与古诗文有些接触。蝉,为很多文人雅士所歌咏。文人听到似断还续的蝉鸣,顿觉悲凉,遂把一腔愁绪、两样离情转嫁于蝉。像孟浩然的“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王维的“倚杖柴门外,临风听暮蝉”,还有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读后让人生出悲凉凄苦之联想。也有例外,唐代诗人虞世南写的《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这是一首托物寓意小诗,诗人以蝉自况,称君子应像蝉一样居高而声远,表现出一种豁达不拘、雍容不迫的气韵风范;沈德潜赞曰“咏蝉者每咏其声,此独尊其品格”,这首诗带给人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其风格寓意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此刻,蝉声依然。在乡下听蝉,生活惬意而直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