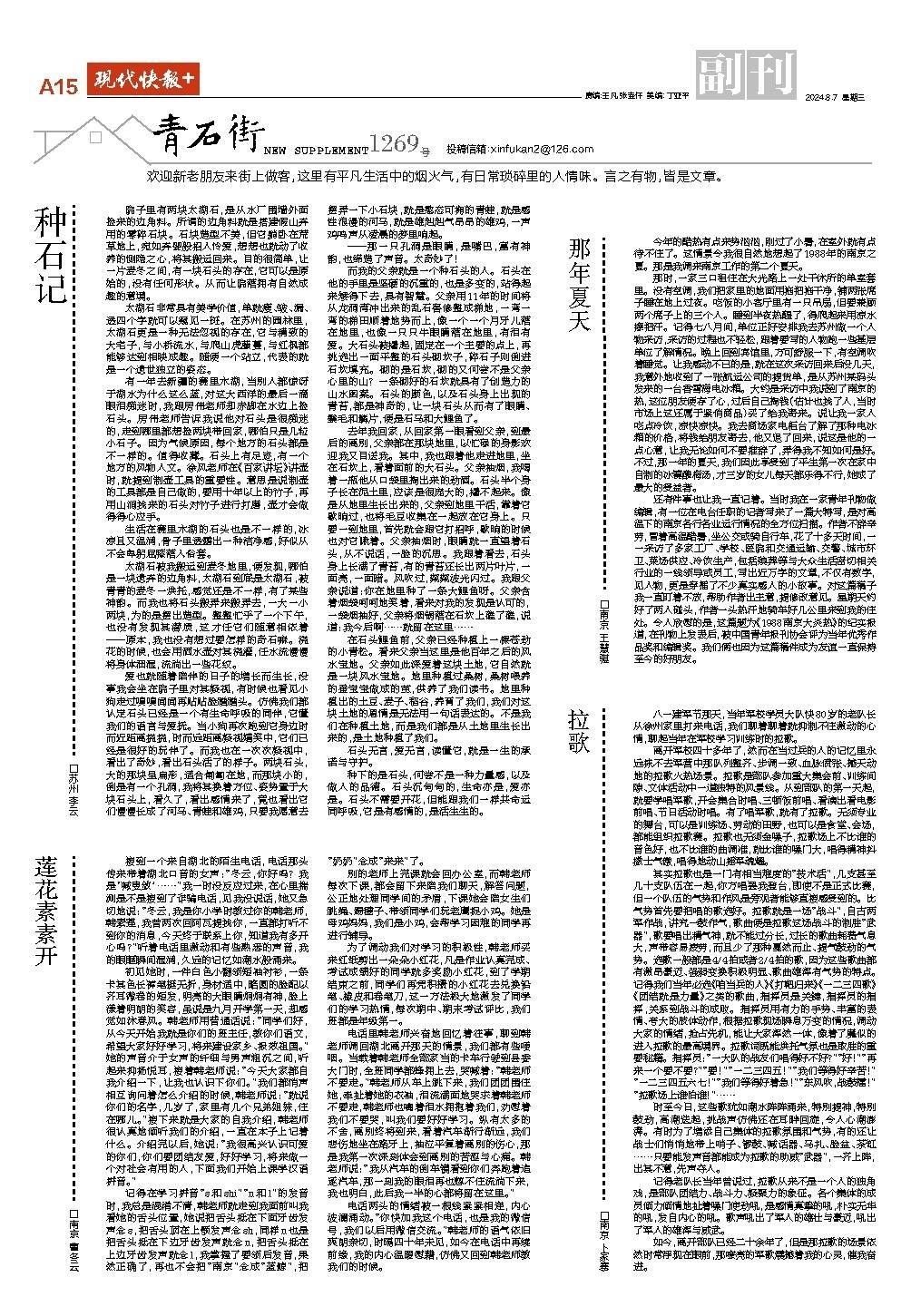□苏州 李云
院子里有两块太湖石,是从水厂围墙外面捡来的边角料。所谓的边角料就是搭建假山弃用的零碎石块。石块造型不美,但它躺卧在荒草地上,宛如弃婴般招人怜爱,想想也就动了收养的恻隐之心,将其搬运回来。目的很简单,让一片麦冬之间,有一块石头的存在,它可以是原始的,没有任何形状。从而让院落拥有自然成趣的意境。
太湖石非常具有美学价值,单就瘦、皱、漏、透四个字就可以窥见一斑。在苏州的园林里,太湖石更是一种无法忽视的存在,它与精致的大宅子,与小桥流水,与爬山虎藤蔓,与红枫都能够达到相映成趣。随便一个站立,代表的就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姿态。
有一年去新疆的赛里木湖,当别人都惊讶于湖水为什么这么蓝,对这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痴迷时,我跟房伟老师却赤脚在水边上捡石头。房伟老师告诉我说他对石头是很痴迷的,走到哪里都想捡两块带回家,哪怕只是几粒小石子。因为气候原因,每个地方的石头都是不一样的。值得收藏。石头上有足迹,有一个地方的风物人文。徐风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壶时,就提到制壶工具的重要性。意思是说制壶的工具都是自己做的,要用十年以上的竹子,再用山涧找来的石头对竹子进行打磨,壶才会做得得心应手。
生活在赛里木湖的石头也是不一样的,冰凉且又温润,骨子里透露出一种洁净感,好似从不会卑躬屈膝落入俗套。
太湖石被我搬运到麦冬地里,便发现,哪怕是一块遗弃的边角料,太湖石到底是太湖石,被青青的麦冬一烘托,感觉还是不一样,有了某些神韵。而我也将石头搬弄来搬弄去,一大一小两块,为的是摆出造型。整整忙乎了一个下午,也没有发现其潜质,这才任它们随意相依着——原本,我也没有想过要怎样的奇石嘛。浇花的时候,也会用洒水壶对其浇灌,任水流慢慢将身体洇湿,流淌出一些花纹。
爱也就随着陪伴的日子的增长而生长,没事我会坐在院子里对其凝视,有时候也看见小狗走过嗅嗅闻闻再贴贴脸蹭蹭头。仿佛我们都认定石头已经是一个有生命呼吸的同伴,它懂我们的语言与爱抚。当小狗再次跑到它身边时而近距离挠挠,时而远距离凝视嬉笑中,它们已经是很好的玩伴了。而我也在一次次凝视中,看出了奇妙,看出石头活了的样子。两块石头,大的那块呈扁形,适合匍匐在地,而那块小的,倒是有一个孔洞,我将其换着方位、姿势置于大块石头上,看久了,看出感情来了,竟也看出它们慢慢长成了河马、青蛙和雄鸡,只要我愿意去摆弄一下小石块,就是憨态可掬的青蛙,就是感性浪漫的河马,就是雄赳赳气昂昂的雄鸡,一声鸡鸣声从凌晨的梦里响起。
——那一只孔洞是眼睛,是嘴巴,富有神韵,也缔造了声音。太奇妙了!
而我的父亲就是一个种石头的人。石头在他的手里是坚硬的沉重的,也是多变的,站得起来矮得下去,具有智慧。父亲用11年的时间将从龙洞湾冲出来的乱石窖修整成梯地,一弯一弯的梯田顺着地势而上,像一个一个月牙儿落在地里,也像一只只牛眼睛落在地里,有泪有爱。大石头被撬起,固定在一个主要的点上,再挑选出一面平整的石头砌坎子,碎石子则倒进石坎填充。砌的是石坎,砌的又何尝不是父亲心里的山?一条砌好的石坎就具有了创造力的山水图案。石头的颜色,以及石头身上出现的青苔,都是神奇的,让一块石头从而有了眼睛、鬃毛和鳞片,便是石马和大鲤鱼了。
去年我回家,从回家第一眼看到父亲,到最后的离别,父亲都在那块地里,以忙碌的身影欢迎我又目送我。其中,我也跟着他走进地里,坐在石坎上,看着面前的大石头。父亲抽烟,我喝着一瓶他从口袋里掏出来的劲酒。石头半个身子长在泥土里,应该是很庞大的,撬不起来。像是从地里生长出来的,父亲到地里干活,靠着它歇晌过,也将毛豆收集在一起放在它身上。只要一到地里,首先就会跟它打招呼,歇晌的时候也对它瞅着。父亲抽烟时,眼睛就一直望着石头,从不说话,一脸的沉思。我跟着看去,石头身上长满了青苔,有的青苔还长出两片叶片,一面亮,一面暗。风吹过,粼粼波光闪过。我跟父亲说道:你在地里种了一条大鲤鱼呀。父亲含着烟袋呵呵地笑着,看来对我的发现是认可的,一袋烟抽好,父亲将烟锅落在石坎上磕了磕,说道:我今后啊……就留在这里……
在石头鲤鱼前,父亲已经种植上一棵苍劲的小青松。看来父亲当这里是他百年之后的风水宝地。父亲如此深爱着这块土地,它自然就是一块风水宝地。地里种植过桑树,桑树喂养的蚕宝宝做成的茧,供养了我们读书。地里种植出的土豆、麦子、稻谷,养育了我们,我们对这块土地的恩情是无法用一句话表达的。不是我们在种植土地,而是我们都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是土地种植了我们。
石头无言,爱无言,读懂它,就是一生的承诺与守护。
种下的是石头,何尝不是一种力量感,以及做人的品德。石头沉甸甸的,生命亦是,爱亦是。石头不需要开花,但能跟我们一样共命运同呼吸,它是有感情的,是活生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