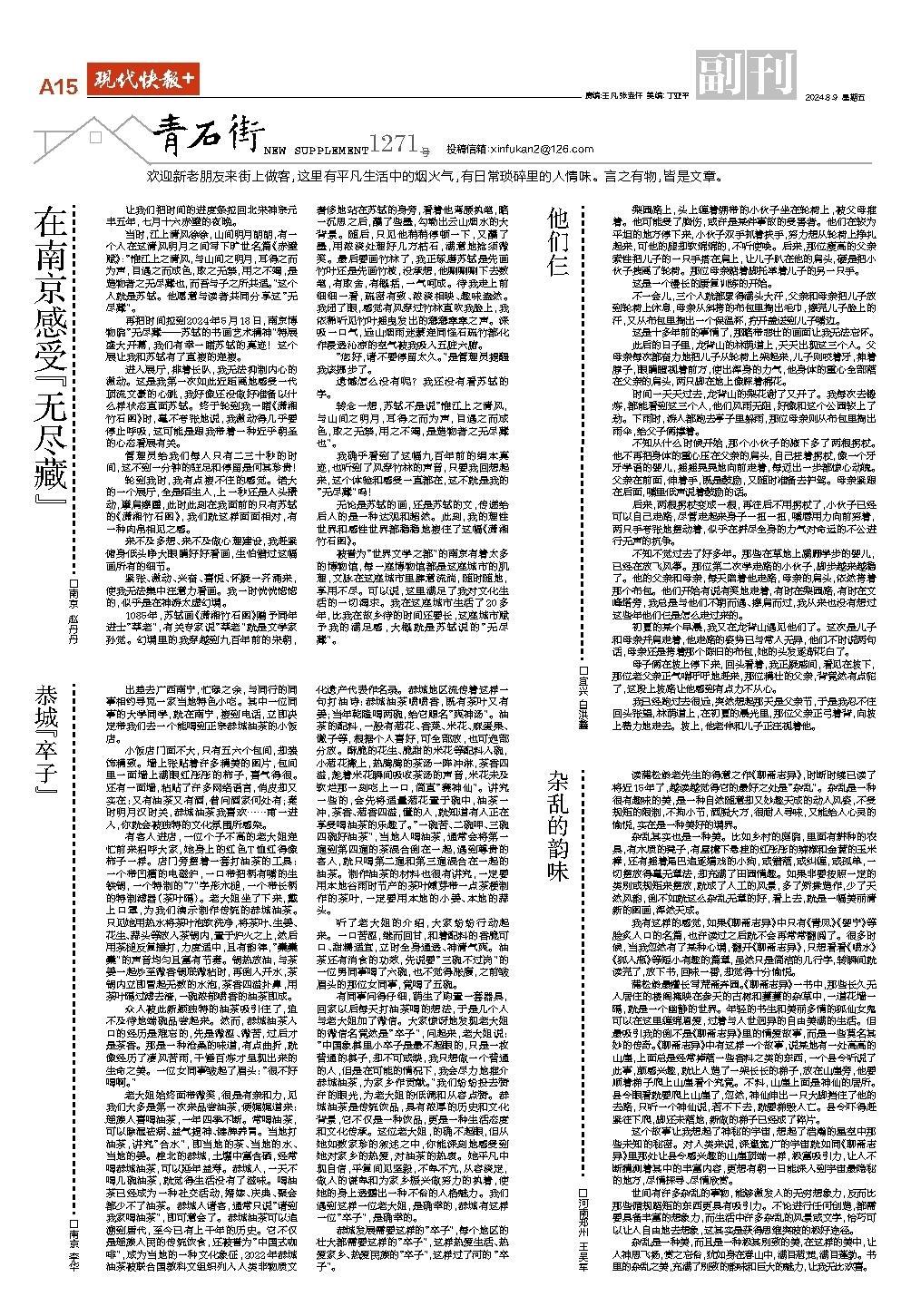□南京 赵丹丹
让我们把时间的进度条拉回北宋神宗元丰五年,七月十六赤壁的夜晚。
当时,江上清风徐徐,山间明月朗朗,有一个人在这清风明月之间写下旷世名篇《赤壁赋》:“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这个人就是苏轼。他愿意与读者共同分享这“无尽藏”。
再把时间拉到2024年5月18日,南京博物院“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特展盛大开幕,我们有幸一睹苏轼的真迹!这个展让我和苏轼有了直接的连接。
进入展厅,排着长队,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一代顶流文豪的心跳,我好像还没做好准备以什么样状态直面苏轼。终于轮到我一睹《潇湘竹石图》时,毫不夸张地说,我激动得几乎要停止呼吸,这可能是跟我带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态看展有关。
管理员给我们每人只有二三十秒的时间,这不到一分钟的驻足和停留是何其珍贵!
轮到我时,我有点接不住的感觉。偌大的一个展厅,全是陌生人,上一秒还是人头攒动,摩肩擦踵,此时此刻在我面前的只有苏轼的《潇湘竹石图》,我们就这样面面相对,有一种肉帛相见之感。
来不及多想、来不及做心理建设,我赶紧俯身低头睁大眼睛好好看画,生怕错过这幅画所有的细节。
紧张、激动、兴奋、喜悦、怀疑一齐涌来,使我无法集中注意力看画。我一时恍恍惚惚的,似乎是在神游太虚幻境。
1085年,苏轼画《潇湘竹石图》赠予同年进士“莘老”,有关专家说“莘老”就是文学家孙觉。幻境里的我穿越到九百年前的宋朝,奢侈地站在苏轼的身旁,看着他弯腰执笔,略一沉思之后,蘸了些墨,勾勒出云山烟水的大背景。随后,只见他稍稍停顿一下,又蘸了墨,用浓淡处理好几方枯石,满意地捻须微笑。最后要画竹林了,我正琢磨苏轼是先画竹叶还是先画竹枝,没承想,他唰唰唰下去数笔,有取舍,有概括,一气呵成。待我走上前细细一看,疏密有致、浓淡相映、趣味盎然。我闭了眼,感觉有风穿过竹林直吹我脸上,我依稀听见竹叶摇曳发出的窸窸窣窣之声。深吸一口气,远山烟雨迷蒙连同怪石疏竹都化作浸透沁凉的空气被我吸入五脏六腑。
“您好,请不要停留太久。”是管理员提醒我该挪步了。
遗憾怎么没有呢?我还没有看苏轼的字。
转念一想,苏轼不是说“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我确乎看到了这幅九百年前的绢本真迹,也听到了风穿竹林的声音,只要我回想起来,这个体验和感受一直都在,这不就是我的“无尽藏”吗!
无论是苏轼的画,还是苏轼的文,传递给后人的是一种达观和超然。此刻,我的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都稳稳地接住了这幅《潇湘竹石图》。
被誉为“世界文学之都”的南京有着太多的博物馆,每一座博物馆都是这座城市的肌理,文脉在这座城市里肆意流淌,随时随地,享用不尽。可以说,这里满足了我对文化生活的一切渴求。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20多年,比我在故乡待的时间还要长,这座城市赋予我的满足感,大概就是苏轼说的“无尽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