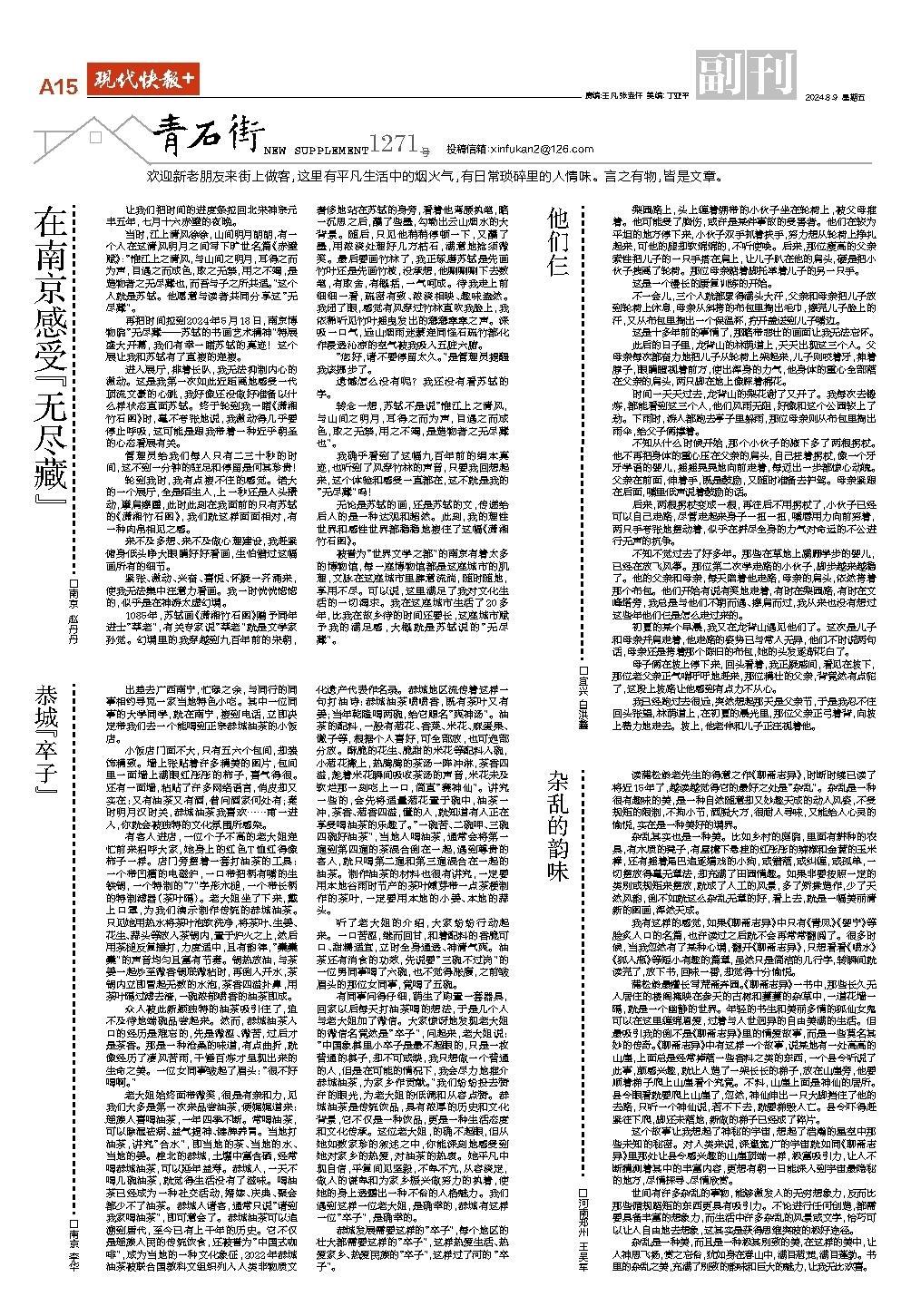□宜兴 白洪鑫
梨园路上,头上缠着绷带的小伙子坐在轮椅上,被父母推着。他可能受了脑伤,或许是某件事故的受害者。他们在较为平坦的地方停下来,小伙子双手抓着扶手,努力想从轮椅上挣扎起来,可他的腿却软绵绵的,不听使唤。后来,那位瘦高的父亲索性把儿子的一只手搭在肩上,让儿子趴在他的肩头,硬是把小伙子拽离了轮椅。那位母亲踮着脚托举着儿子的另一只手。
这是一个漫长的康复训练的开始。
不一会儿,三个人就都累得满头大汗,父亲和母亲把儿子放到轮椅上休息,母亲从斜挎的布包里掏出毛巾,擦完儿子脸上的汗,又从布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拧开盖送到儿子嘴边。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那略带悲壮的画面让我无法忘怀。
此后的日子里,龙背山的林荫道上,天天出现这三个人。父母亲每次都奋力地把儿子从轮椅上架起来,儿子则咬着牙,抻着脖子,眼睛瞪视着前方,使出浑身的力气,他身体的重心全部落在父亲的肩头,两只脚在地上像踩着棉花。
时间一天天过去,龙背山的梨花谢了又开了。我每次去锻炼,都能看到这三个人,他们风雨无阻,好像和这个公园较上了劲。下雨时,游人都跑去亭子里躲雨,那位母亲则从布包里掏出雨伞,给父子俩撑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个小伙子的腋下多了两根拐杖。他不再把身体的重心压在父亲的肩头,自己拄着拐杖,像一个牙牙学语的婴儿,摇摇晃晃地向前走着,每迈出一步都惊心动魄。父亲在前面,伸着手,既是鼓励,又随时准备去护驾。母亲紧跟在后面,嘴里低声说着鼓励的话。
后来,两根拐杖变成一根,再往后不用拐杖了,小伙子已经可以自己走路,尽管走起来身子一扭一扭,嘴唇用力向前努着,两只手夸张地摆动着,似乎在拼尽全身的力气对命运的不公进行无声的抗争。
不知不觉过去了好多年。那些在草地上蹒跚学步的婴儿,已经在放飞风筝。那位第二次学走路的小伙子,脚步越来越稳了。他的父亲和母亲,每天陪着他走路,母亲的肩头,依然挎着那个布包。他们开始有说有笑地走着,有时在梨园路,有时在文峰塔旁,我总是与他们不期而遇、擦肩而过,我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些年他们仨是怎么走过来的。
初夏的某个早晨,我又在龙背山遇见他们了。这次是儿子和母亲并肩走着,他走路的姿势已与常人无异,他们不时说两句话,母亲还是挎着那个陈旧的布包,她的头发逐渐花白了。
母子俩在坡上停下来,回头看着,我正疑惑间,看见在坡下,那位老父亲正气喘吁吁地赶来,那位精壮的父亲,背竟然有点驼了,这段上坡路让他感到有点力不从心。
我已经跑过去很远,突然想起那天是父亲节,于是我忍不住回头张望,林荫道上,在初夏的晨光里,那位父亲正弓着背,向坡上费力地走去。坡上,他老伴和儿子正注视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