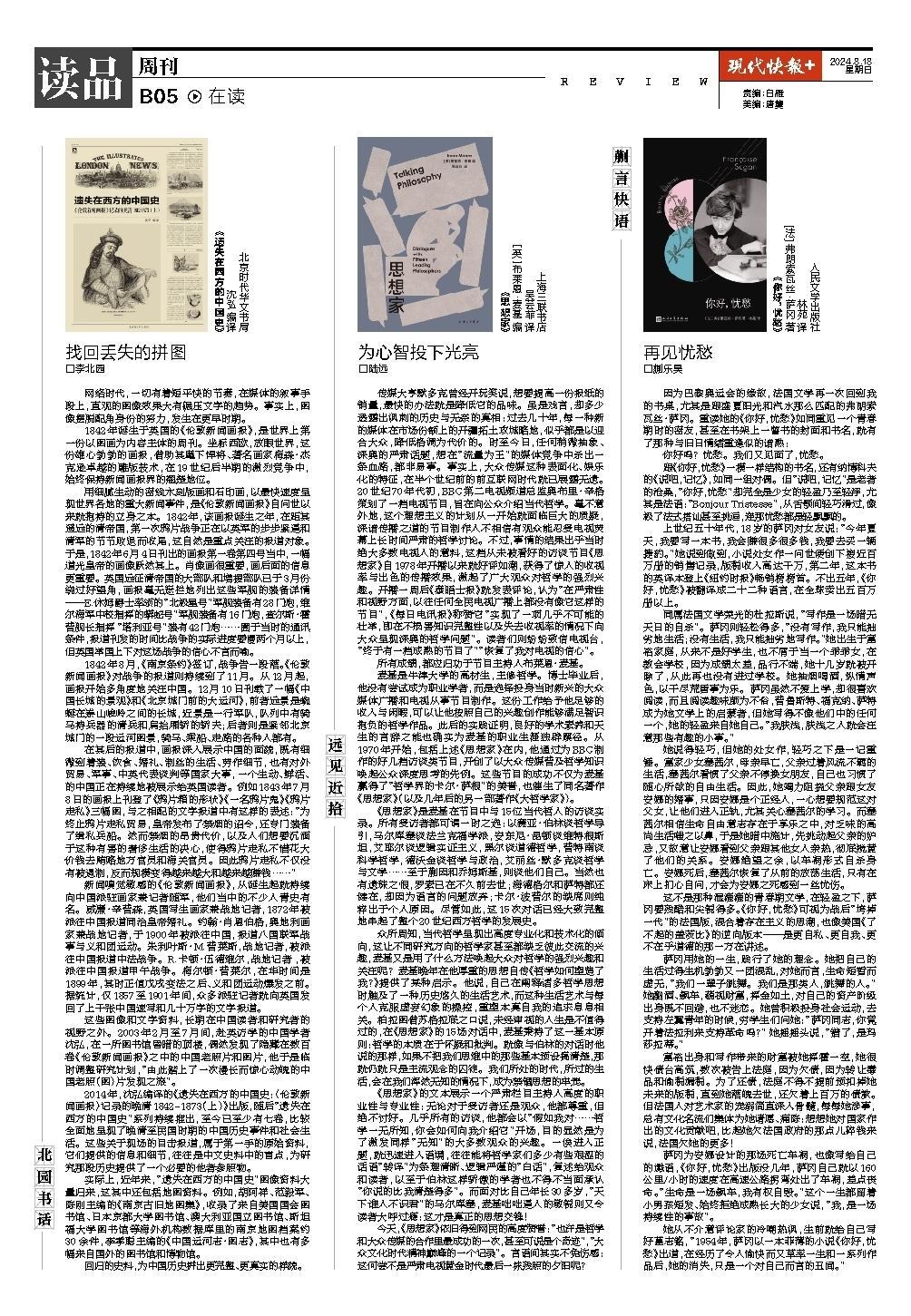□李北园
网络时代,一切有着短平快的节奏,在媒体的叙事手段上,直观的图像效果大有碾压文字的趋势。事实上,图像摆脱配角身份的努力,发生在更早时期。
1842年诞生于英国的《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上第一份以图画为内容主体的周刊。坐标西欧,放眼世界,这份雄心勃勃的画报,借助其麾下悍将、著名画家梅森·杰克逊卓越的雕版技术,在19世纪后半期的激烈竞争中,始终保持新闻画报界的翘楚地位。
用细腻生动的密线木刻版画和石印画,以最快速度呈现世界各地的重大新闻事件,是《伦敦新闻画报》自问世以来就抱持的立身之本。1842年,该画报诞生之年,在距其遥远的清帝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在以英军的步步紧逼和清军的节节败退而收尾,这自然是重点关注的报道对象。于是,1842年6月4日刊出的画报第一卷第四号当中,一幅道光皇帝的画像跃然其上。肖像画很重要,画后面的信息更重要。英国远征清帝国的大部队和增援部队已于3月份绕过好望角,画报毫无遮拦地列出这些军舰的装备详情——E.休姆爵士率领的“北极星号”军舰装备有28门炮,维尔海军中校指挥的蟒蛇号”军舰装备有16门炮,查尔斯·霍普舰长指挥 “塔利亚号”装有42门炮……囿于当时的通讯条件,报道刊发的时间比战争的实际进度要慢两个月以上,但英国举国上下对这场战争的信心不言而喻。
1842年8月,《南京条约》签订,战争告一段落。《伦敦新闻画报》对战争的报道则持续到了11月。从12月起,画报开始多角度地关注中国。12月10日刊载了一幅《中国长城的景观》和《北京城门前的大运河》,前者远景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长城,近景是一行军队,队列中有骑马持兵器的清兵和肩抬厢轿的轿夫;后者则是紧邻北京城门的一段运河图景,骑马、乘船、走路的各种人都有。
在其后的报道中,画报深入展示中国的面貌,既有细微到着装、饮食、婚礼、制丝的生活、劳作细节,也有对外贸易、军事、中英代表谈判等国家大事,一个生动、鲜活、的中国正在持续地被展示给英国读者。例如1843年7月8日的画报上刊登了《鸦片箱的形状》《一名鸦片鬼》《鸦片走私》三幅图,与之相配的文字报道中有这样的表述:“为终止鸦片走私贸易,皇帝发布了禁烟的诏令,还专门装备了缉私兵船。然而禁烟的昂贵代价,以及人们想要沉湎于这种有害的奢侈生活的决心,使得鸦片走私不惜花大价钱去贿赂地方官员和海关官员。因此鸦片走私不仅没有被遏制,反而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和越来越赚钱……”
新闻嗅觉敏感的《伦敦新闻画报》,从诞生起就持续向中国派驻画家兼记者随军,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青史有名。威廉·辛普森,英国写生画家兼战地记者,1872年被派往中国报道同治皇帝婚礼。约翰·肖恩伯格,奥地利画家兼战地记者,于1900年被派往中国,报道八国联军战事与义和团运动。朱利叶斯·M.普莱斯,战地记者,被派往中国报道中法战争。R.卡顿·伍德维尔,战地记者 ,被派往中国报道甲午战争。梅尔顿·普莱尔,在华时间是1899年,其时正值戊戌变法之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据统计,仅1857至1901年间,众多派驻记者就向英国发回了上千张中国速写和几十万字的文字报道。
这些图像和文字资料,长期在中国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之外。2003年2月至7月间,赴英访学的中国学者沈弘,在一所图书馆昏暗的顶楼,偶然发现了隐藏在数百卷《伦敦新闻画报》之中的中国老照片和图片,他于是临时调整研究计划,“由此踏上了一次漫长而惊心动魄的中国老照(图)片发现之旅”。
2014年,沈弘编译的《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上)》出版,随后“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持续推出,至今已至少有七卷,比较全面地呈现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这些关于现场的目击报道,属于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它们提供的信息和细节,往往是中文史料中的盲点,为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一个必要的他者参照物。
实际上,近年来,“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图像资料大量归来,这其中还包括地图资料。例如,胡阿祥、范毅军、陈刚主编的《南京古旧地图集》,收录了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等海外机构数据库里的南京地图档案约 30 余件,李孝聪主编的《中国运河志·图志》,其中也有多幅来自国外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回归的史料,为中国历史拼出更完整、更真实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