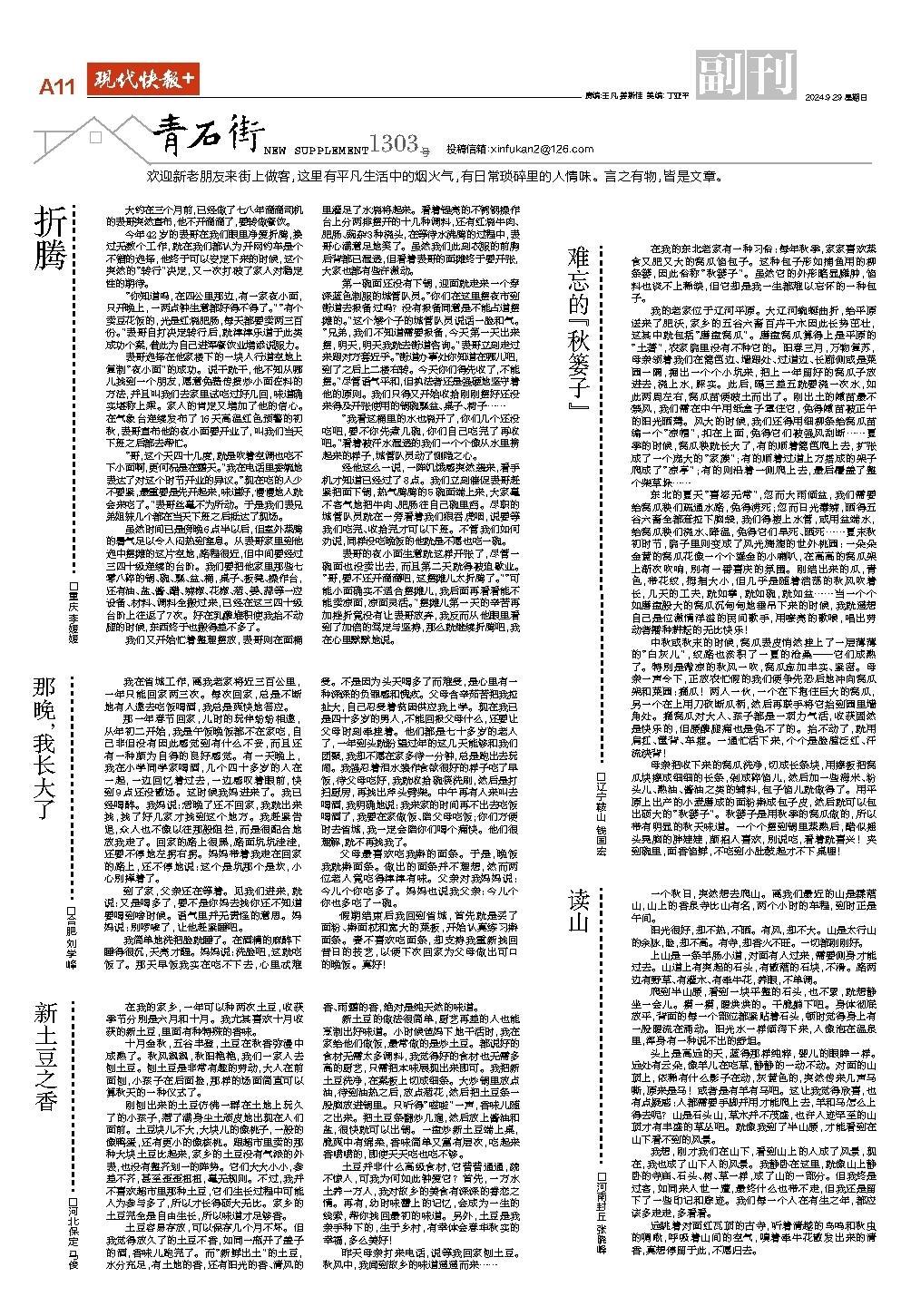□辽宁鞍山 钱国宏
在我的东北老家有一种习俗:每年秋季,家家喜欢蒸食又肥又大的窝瓜馅包子。这种包子形如捕鱼用的柳条篓,因此俗称“秋篓子”。虽然它的外形略显臃肿,馅料也谈不上稀缺,但它却是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一种包子。
我的老家位于辽河平原。大辽河蜿蜒曲折,给平原送来了肥沃,家乡的五谷六畜百卉千木因此长势茁壮,这其中就包括“磨盘窝瓜”。磨盘窝瓜算得上是平原的“土著”,农家院里没有不种它的。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母亲领着我们在篱笆边、墙跟处、过道边、长廊侧或是菜园一隅,掘出一个个小坑来,把上一年留好的窝瓜子放进去,浇上水,踩实。此后,隔三差五就要浇一次水,如此两周左右,窝瓜苗便破土而出了。刚出土的嫩苗最不禁风,我们需在中午用纸盒子罩住它,免得嫩苗被正午的阳光晒蔫。风大的时候,我们还得用细柳条给窝瓜苗编一个“凉帽”,扣在上面,免得它们被强风刮断……夏季的时候,窝瓜秧就长大了,有的顺着篱笆爬上去,扩张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有的顺着过道上方搭成的架子爬成了“凉亭”;有的则沿着一侧爬上去,最后覆盖了整个柴草垛……
东北的夏天“喜怒无常”,忽而大雨倾盆,我们需要给窝瓜秧们疏通水路,免得涝死;忽而日光毒辣,晒得五谷六畜全都耷拉下脑袋,我们得接上水管,或用盆端水,给窝瓜秧们浇水、降温,免得它们旱死、晒死……夏末秋初时节,院子里则变成了风光旖旎的世外桃园:一朵朵金黄的窝瓜花像一个个鎏金的小喇叭,在高高的窝瓜架上渐次吹响,别有一番喜庆的氛围。刚结出来的瓜,青色,带花纹,拇指大小,但几乎是随着浩荡的秋风吹着长,几天的工夫,就如拳,就如碗,就如盆……当一个个如磨盘般大的窝瓜沉甸甸地垂吊下来的时候,我就遥想自己是位激情洋溢的民间歌手,用嘹亮的歌喉,唱出劳动者播种耕耘的无比快乐!
中秋或秋末的时候,窝瓜表皮悄然挂上了一层薄薄的“白灰儿”,纹路也淤积了一夏的沧桑——它们成熟了。特别是微凉的秋风一吹,窝瓜愈加丰实、紧密。母亲一声令下,正放农忙假的我们便争先恐后地冲向窝瓜架和菜园:摘瓜!两人一伙,一个在下抱住巨大的窝瓜,另一个在上用刀砍断瓜柄,然后再联手将它抬到园里墙角处。摘窝瓜对大人、孩子都是一项力气活,收获固然是快乐的,但腰酸腿痛也是免不了的。抬不动了,就用肩扛、筐背、车推。一通忙活下来,个个是脸膛泛红、汗流浃背!
母亲把收下来的窝瓜洗净,切成长条块,用擦板把窝瓜块擦成细细的长条,剁成碎馅儿,然后加一些海米、粉头儿、熟油、酱油之类的辅料,包子馅儿就做得了。用平原上出产的小麦磨成的面粉擀成包子皮,然后就可以包出硕大的“秋篓子”。秋篓子是用秋季的窝瓜做的,所以带有明显的秋天味道。一个个摆到锅里蒸熟后,酷似摇头晃脑的胖娃娃,颇招人喜欢,别说吃,看着就喜兴!夹到碗里,面香馅鲜,不吃到小肚鼓起才不下桌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