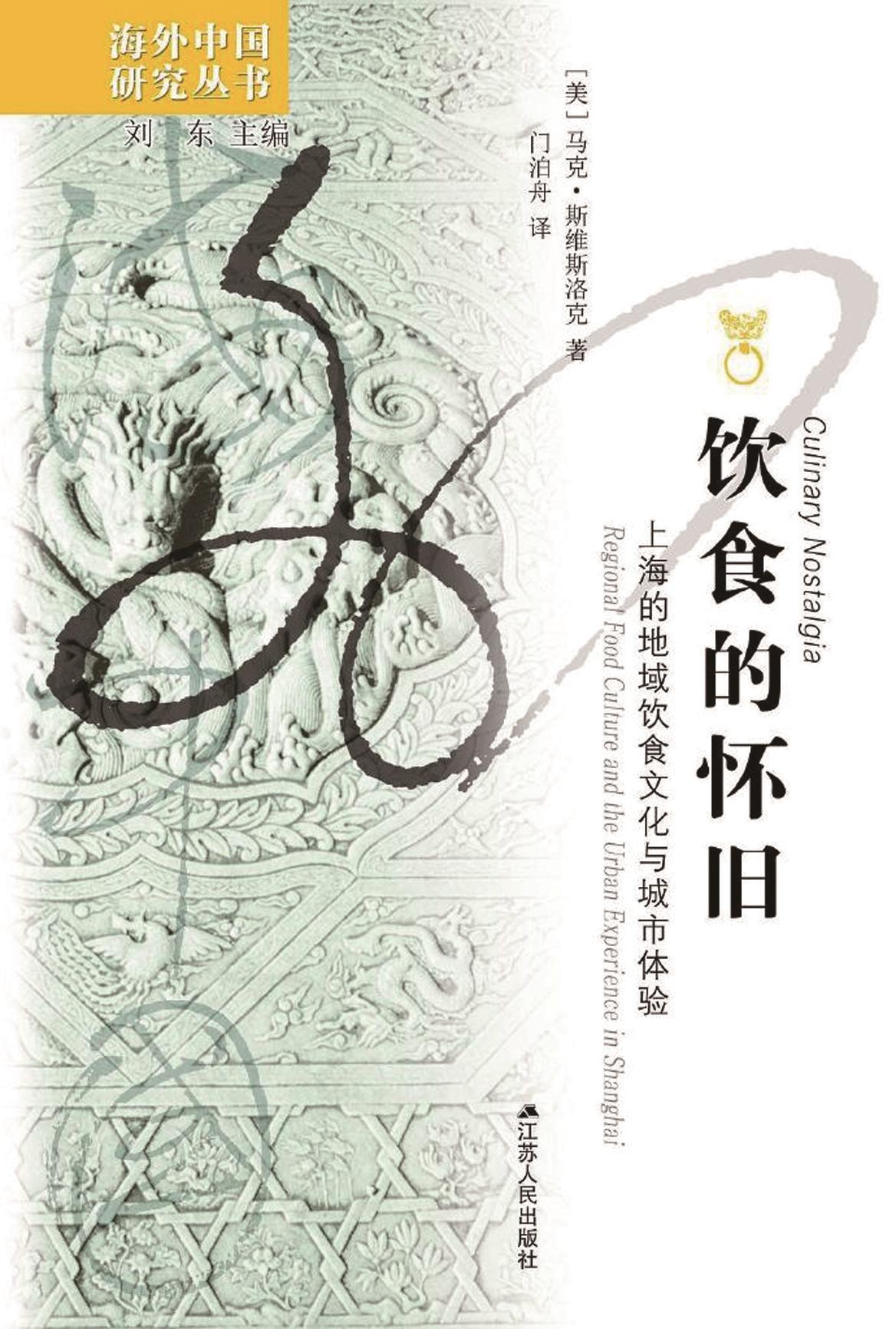□陆远
1911年9月26日,上海当地报纸《时报》刊登了一首《上海著名食品歌》:先得楼的羊肉、一家春的大菜、万有全的火腿、邵万生的南货、杏花楼的宵夜、陆稿荐的酱肉、言茂源的花雕、陆鼎兴的汤包……寥寥数笔,不仅让老饕们闻之垂涎,更把一个城市繁荣的餐饮业和它表征的那个丰富而多元的国际都会烘托得淋漓尽致。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1936年,上海胜利唱片公司为歌舞剧《夜玫瑰》灌制唱片,其中一首插曲《五芳斋》由“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先生创作的歌曲传唱一时,歌词写道:“黄河鲤鱼,青浦芥菜,四川白木耳,福建青海带,北平溜丸子氽汤,那南京烧鸭子来得快。广东叉烧,湖南辣椒,合拢起来炒一炒,辣得很好。云南火腿,山西皮蛋,合拢起来拌一拌,下酒又送饭……”旋律欢快,勾人味蕾。
又过了80多年,老字号“五芳斋”买下这首《五芳斋》老歌的版权,邀请《舌尖上的中国》分集导演,和着当年演唱人周璇、严华、严斐的歌声,打造了一支复古民国风MV,成为2019年春节风靡全网的作品。
在美国学者马克·斯维斯洛克看来,《五芳斋》中散发出的“老上海”怀旧情绪,不过是“这座有着漫长而深刻怀旧传统的城市在其发展史上的最新篇章而已”。而想要探讨上海悠久城市史上这一经典主题,恐怕没什么比饮食文化更有趣的切入点了,因为饮食的变迁正是这座城市种种变迁的缩影。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斯维斯洛克把这座东方大都会作为观察中国人实践都市生活、探寻地方身份、构建国家认同的田野,他发现,天南海北各种“风味”在这座都市的迅速膨胀而此消彼长,中外各色人等的饕餮之欲与饮食习惯,既是城市发展风云变幻中最灵敏的风向标,也是世事浮沉里赓续城市精神的定海针。在其代表作《饮食的怀旧》中,从最早记载上海地区物产的文献,到当下汇聚在这座城市的美食潮流,斯维斯洛克以历史学家的严谨和社会学家的想象力,从饮食史的角度向我们描绘一幅一个半世纪以来活色生香的城市史画卷。
上海的城市性格与文化特征究竟是什么,当然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不过,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1924年无意中发明的那个词“魔都”,倒是提供了一种别具一格的意象:正是明暗之间这种多元而矛盾的状态,赋予了上海城市文化丰富的内涵和无穷的魅力。《饮食的怀旧》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也是由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国家、东方与西方、富豪与贫民、奢华与朴素、男人和女人等种种矛盾交织又充满张力的图景。
在这幅图景中我们看到,早在上海开埠之前好几个世纪,当地的文化精英就尝试着用种种方式要将这个人文遗产并不丰厚的城市纳入中国文明史大背景,特别是江南地区悠久的历史书写传统中,他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符号,是一种本地独有的水蜜桃。我们接着看到,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启了国际化的序幕,租界的出现和华洋杂处的格局,让这座城市形成了两种有着相反意涵的形象:摩登的租界区和古老的老城厢,饮食差异正是二者重要的分水岭。在这一过程中,餐馆扮演了重要角色,它用人们最熟悉的方式,既揭示了不同国度、不同地域、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又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我们继续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兴起的“西餐热”(1899年,四马路上的西餐馆的数量比各式中国地方餐馆加起来的总数还要多)深刻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和人们关于城市的观念。沪上风月场中人在吃西餐这件事上展示了高超的技巧,成为新时尚的弄潮儿,而对另一些中国人来说,西餐不仅烹饪方法粗糙,味道令人作呕,并且道德有亏(重要的理由是西餐中大量使用牛肉,而中国人无论从宗教还是世俗伦理出发,都不倡导使用牛肉)。我们还能看到,20世纪20年代上海成为北京之外最重要的文化中心,饮食也成为不同阶层不同类型文化人与城市建立联系的方式:严独鹤那样的上层精英,通过在美食世界的漫游,传达对城市文化的掌控感;叶圣陶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借着怀念家乡清晰自然的食物,反思上海滩的光怪陆离;王定九的上海指南系列,则以丰富的细节和轶事,提供了描绘上海饮食文化的另一种话语范式。至于1949年以后,“转向社会主义”的上海饮食文化如何在艰苦朴素和繁荣富足之间寻求平衡;改革开放之后,“本邦菜”的兴起如何重塑了“海派”文化意象,书中都有精彩的故事。
作为西方世界第一部系统探讨中国地域饮食文化的作品,《饮食的怀旧》告诉我们,饮食是中国人追忆过往、思考当下和想象未来的载体,还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