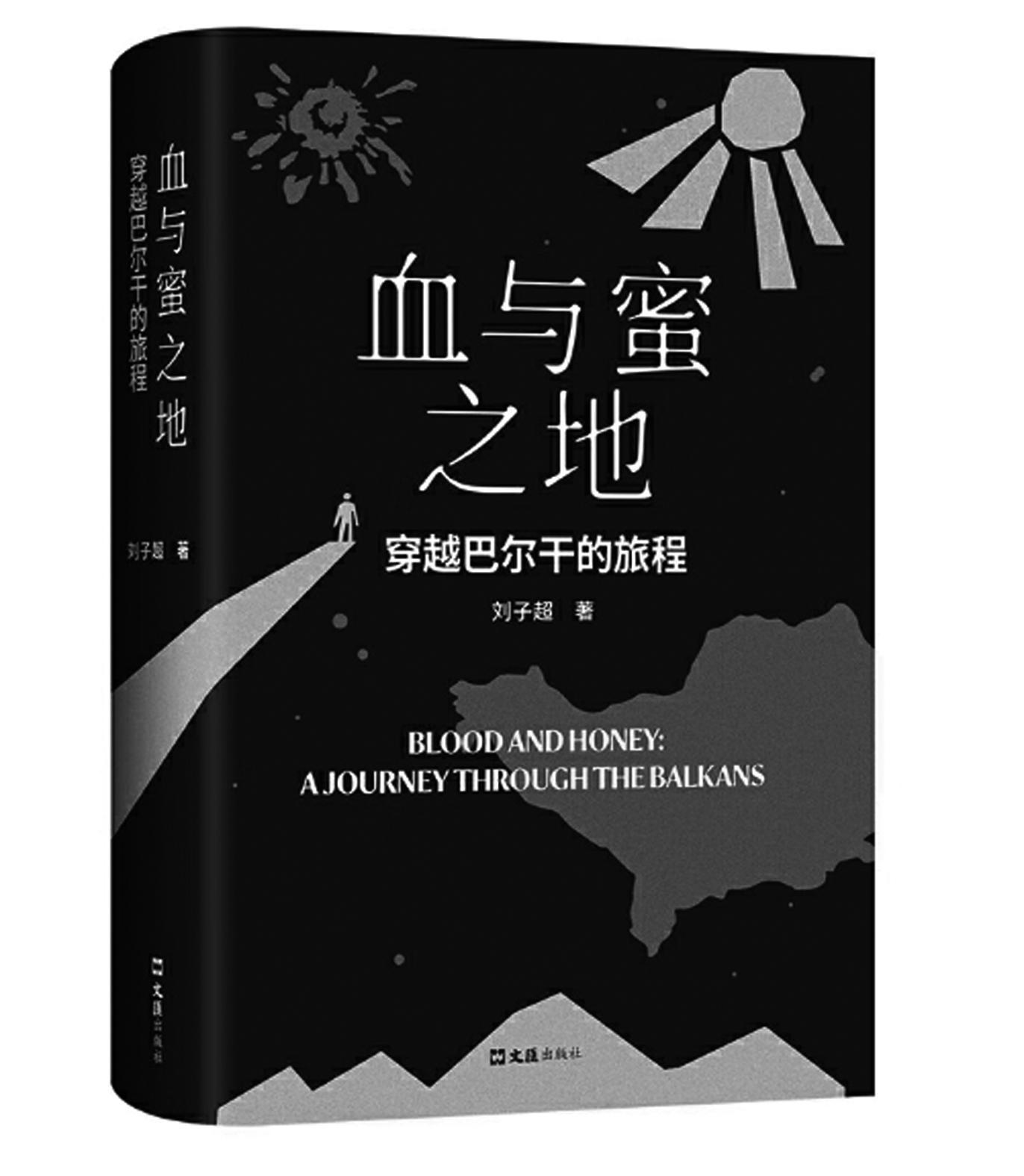□林颐
刘子超专注旅行写作十余年,目前已出版作品四部:《沿着季风的方向》《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午夜降临前抵达》以及新作《血与蜜之地:穿越巴尔干的旅程》。
以这个时间长度和出版数量来说,刘子超相当节制且保持了稳定的进取心。从这些作品所显示的旅行区域来看,东南亚、中亚、中欧、巴尔干都有着独特的异域风光和悠久的人文历史,这种偏好显示了刘子超明确的旅行目的,不是无所事事的漫游,而是有规划的一种实践,在这种实践中获得自我的省思和对世界深刻明晰的认识。
读刘子超的作品,很容易感觉到他对阅读的喜爱。阅读能够作为旅行的充分准备,收集信息,积累历史文化常识,这使得他的旅行张弛有度、从容自如。《黑羊与灰鹰:巴尔干六百年,一次苦难与希望的探索之旅》《巴尔干两千年:穿越历史的幽灵》《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大部分作品与巴尔干的历史、现状有着紧密联系,或是作者思维发散所牵系的片言只语,这些引用增加了《血与蜜之地》的内涵和厚度。
“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一种经验催生另一种经验——这正是旅行和阅读的美妙之处。”刘子超沉浸于阅读,也执着于进入现场。《血与蜜之地》后记有言:“旅行写作的核心,不仅是从外部旁观,更需要深入接触和理解那里的人。书写人类的命运如何在漫长的时间、记忆和地理的褶皱中发挥作用,正是旅行写作所要追寻的目标。”
从的里雅斯特启程,穿越巴尔干半岛,最终抵达半岛最南端的城市——雅典。刘子超尝试建立一种双线叙事的策略:一条是以自己的旅程为线索,穿插讲述以往阅读中获得的知识,呈现巴尔干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另一条则是尽力描述与所经之地的人们的现场谈话,透过当地人的视线去理解巴尔干的社会变迁。也就是说,刘子超着眼于自身“局外人”的观察,同时借助“局内人”的生活经验来修正自己的看法,正因如此,刘子超的游记脱离了浮光掠影的观光,而成为具有实在的思辨色彩的人文作品。
巴尔干是“血与蜜之地”,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巴尔干,其实是近两百年形成的概念,在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才形成的。民族主义让巴尔干半岛诸国相继崛起,纷纷立国,然而,正是民族主义让巴尔干半岛很快陷入了暴力,整个20世纪,这里爆发过五次大规模的战争,伴随着屠杀、种族清洗、难民潮和人口交换。
距我们较近的这一次发生在1990年代。当时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北约的精确制导导弹击中,这一事件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发生在遥远之地的战争并非与我们全然无关,在全球化时代,每一次蝴蝶翅膀的振动可能都会掀起海啸。也正是这一次事件,促使刘子超在若干年后启程前往巴尔干,在此时此地深刻体验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复杂面相,在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各族群人们的接触中传达出他们的共存与对立、他们被撕裂的疼痛、他们对往昔时光的眷恋与未来的想象。
很多场景,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比如,刘子超探访一座葡萄园,边境线恰巧从葡萄庄园的中间穿过。在农宅的石墙墙面上有一条黄色的直线,意大利落在黄线的一侧,南斯拉夫落在另一侧。在主人的娓娓讲述中,我们知道了一些葡萄园的历史,这座庄园的所属权是被南斯拉夫的命运以及国家的解体所决定的。关于分界线的故事,在后面不同人的讲述中还出现了好几次,其中有人说起自己童年对分界线的好奇心,他曾经偷偷穿越分界线以试图弄清对面的人能否知道他是“异类”。人们都是怎么判断族群身份的呢?
分界线是无形的、人为的,而它又是森严的规则,昭示着难以修补的深切裂痕。巴尔干的人们对于自身困境的迷茫,也在提醒着我们对“民族主义”的思考。何以为“家”?如何区分“他者”和“我者”?是什么在联结“我们”?旅行的意义之一,就是摆脱自我的囿制环境和思维定势,在倾听各种声音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内在、定义你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