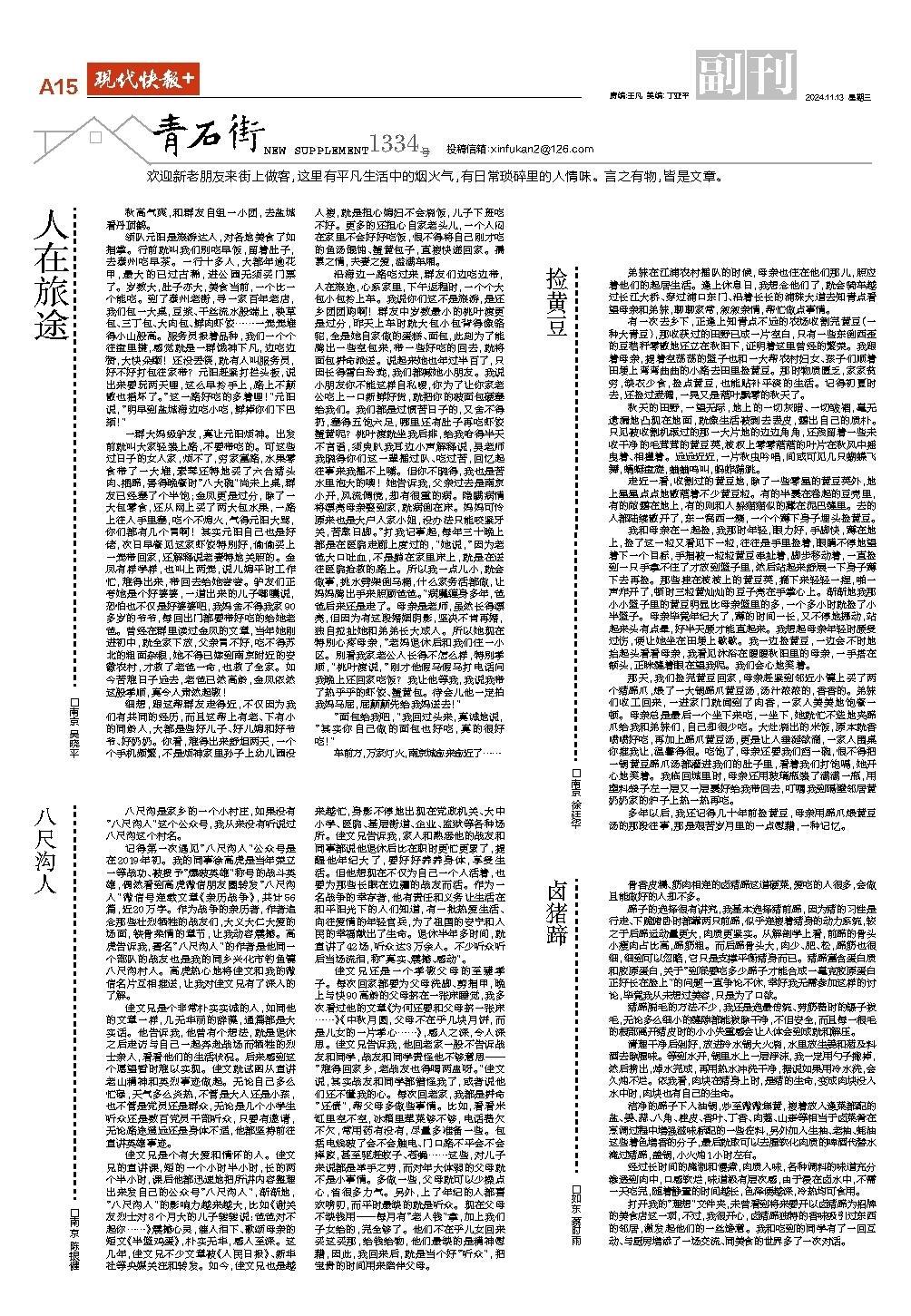□南京 徐廷华
弟妹在江浦农村插队的时候,母亲也住在他们那儿,照应着他们的起居生活。逢上休息日,我想念他们了,就会骑车越过长江大桥、穿过浦口东门、沿着长长的浦珠大道去知青点看望母亲和弟妹,聊聊家常,叙叙亲情,帮忙做点事情。
有一次去乡下,正逢上知青点不远的农场收割完黄豆(一种大青豆),那收获过的田野已成一片空白,只有一些东倒西歪的豆秸秆零散地还立在秋阳下,证明着这里曾经的繁荣。我跟着母亲,提着空荡荡的篮子也和一大帮农村妇女、孩子们顺着田埂上弯弯曲曲的小路去田里捡黄豆。那时物质匮乏,家家贫穷,缺衣少食,捡点黄豆,也能贴补平淡的生活。记得初夏时去,还捡过麦穗,一晃又是落叶飘零的秋天了。
秋天的田野,一望无际,地上的一切灰暗、一切皱褶,毫无遗漏地凸现在地面,就像生活被剥去表皮,露出自己的质朴。只见被收割机滚过的那一大片地的边边角角,还残留着一些未收干净的毛茸茸的黄豆荚,枝杈上零零落落的叶片在秋风中摇曳着、相撞着。远远近近,一片秋虫吟唱,间或可见几只蝴蝶飞舞,蜻蜓盘旋,蛐蛐鸣叫,蚂蚱蹦跳。
走近一看,收割过的黄豆地,除了一些零星的黄豆荚外,地上星星点点地散落着不少黄豆粒。有的半裹在卷起的豆壳里,有的敞露在地上,有的则和人躲猫猫似的藏在泥巴缝里。去的人都陆续散开了,东一窝西一簇,一个个蹲下身子埋头捡黄豆。
我和母亲在一起捡,我那时年轻,眼力好,手脚快,蹲在地上,捡了这一粒又看见下一粒,往往是手里捡着,眼睛不停地望着下一个目标,手指被一粒粒黄豆牵扯着,脚步移动着,一直捡到一只手拿不住了才放到篮子里,然后站起来舒展一下身子蹲下去再捡。那些挂在枝枝上的黄豆荚,摘下来轻轻一捏,啪一声炸开了,顿时三粒黄灿灿的豆子亮在手掌心上。渐渐地我那小小篮子里的黄豆明显比母亲篮里的多,一个多小时就捡了小半篮子。母亲毕竟年纪大了,蹲的时间一长,又不停地挪动,站起来头有点晕,好半天腰才能直起来。我想起母亲年轻时腰受过伤,便让她坐在田埂上歇歇。我一边捡黄豆,一边会不时地抬起头看看母亲,我看见沐浴在暖暖秋阳里的母亲,一手搭在额头,正眯缝着眼在望我呢。我们会心地笑着。
那天,我们捡完黄豆回家,母亲赶紧到邻近小镇上买了两个猪蹄爪,煨了一大锅蹄爪黄豆汤,汤汁浓浓的,香香的。弟妹们收工回来,一进家门就闻到了肉香,一家人美美地饱餐一顿。母亲总是最后一个坐下来吃,一坐下,她就忙不迭地夹蹄爪给我和弟妹们,自己却很少吃。大灶烧出的米饭,原本就香喷喷好吃,再加上蹄爪黄豆汤,更是让人垂涎欲滴,一家人围桌你推我让,温馨得很。吃饱了,母亲还要我们舀一碗,恨不得把一锅黄豆蹄爪汤都灌进我们的肚子里,看着我们打饱嗝,她开心地笑着。我临回城里时,母亲还用玻璃瓶装了满满一瓶,用塑料袋子左一层又一层裹好给我带回去,叮嘱我到隔壁邻居黄奶奶家的炉子上热一热再吃。
多年以后,我还记得几十年前捡黄豆,母亲用蹄爪煨黄豆汤的那段往事,那是艰苦岁月里的一点慰藉,一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