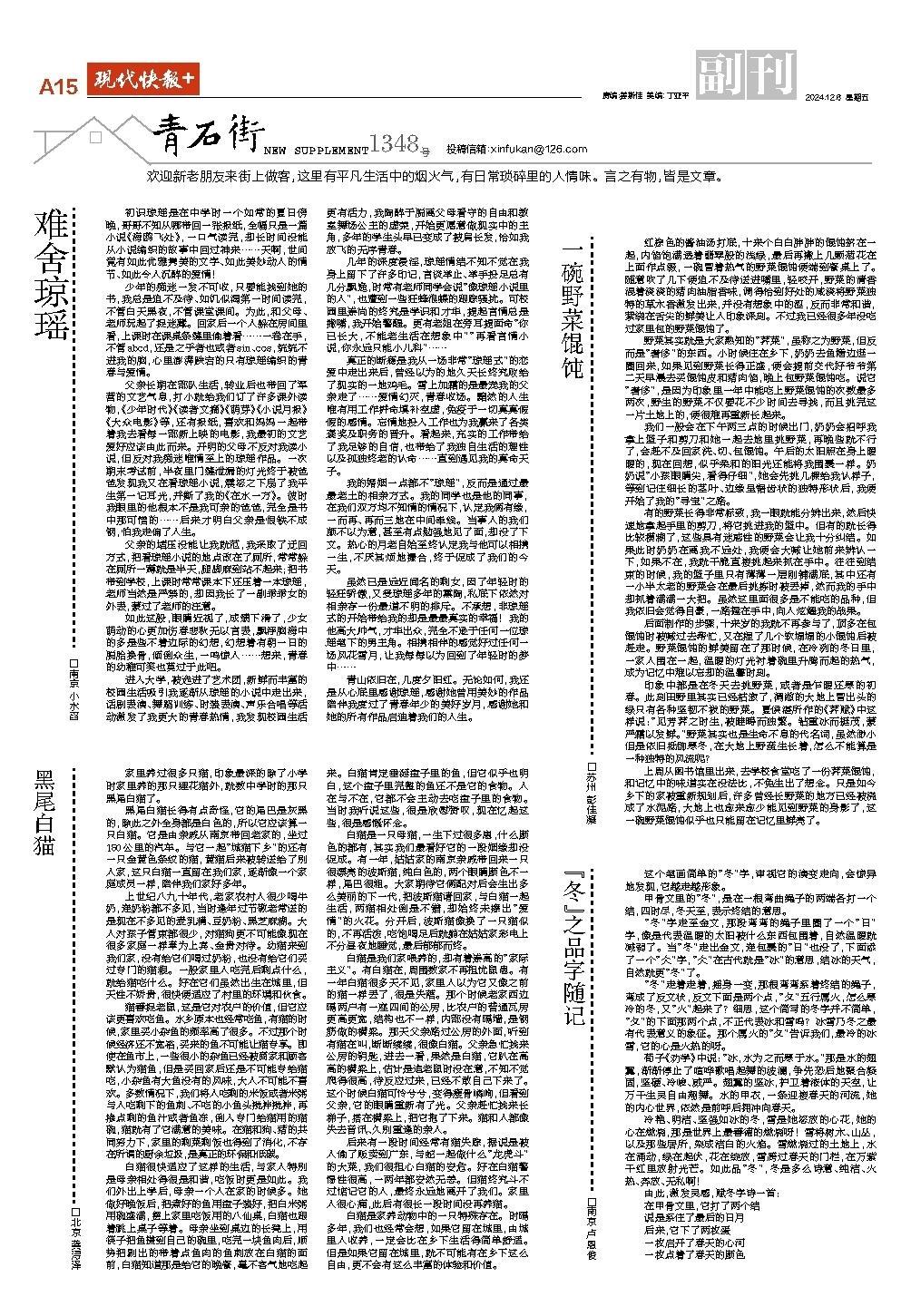□苏州 彭佳凝
红棕色的酱油汤打底,十来个白白胖胖的馄饨挤在一起,内馅饱满透着翡翠般的浅绿,最后再撒上几颗葱花在上面作点缀,一碗冒着热气的野菜馄饨便端到餐桌上了。随意吹了几下便迫不及待送进嘴里,轻咬开,野菜的清香混着淡淡的猪肉油脂香味,调得恰到好处的咸淡将野菜独特的草木香激发出来,并没有想象中的涩,反而非常和谐,萦绕在舌尖的鲜美让人印象深刻。不过我已经很多年没吃过家里包的野菜馄饨了。
野菜其实就是大家熟知的“荠菜”,虽称之为野菜,但反而是“奢侈”的东西。小时候住在乡下,奶奶去鱼塘边逛一圈回来,如果见到野菜长得正盛,便会提前交代好爷爷第二天早晨去买馄饨皮和猪肉馅,晚上包野菜馄饨吃。说它“奢侈”,是因为印象里一年中能吃上野菜馄饨的次数最多两次,野生的野菜不仅要花不少时间去寻找,而且挑完这一片土地上的,便很难再重新长起来。
我们一般会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出门,奶奶会招呼我拿上篮子和剪刀和她一起去地里挑野菜,再晚些就不行了,会赶不及回家洗、切、包馄饨。午后的太阳照在身上暖暖的,现在回想,似乎柔和的阳光还能将我围裹一样。奶奶说“小孩眼睛尖,看得仔细”,她会先挑几棵给我认样子,等到记住细长的茎叶、边缘呈锯齿状的独特形状后,我便开始了我的“寻宝”之路。
有的野菜长得非常标致,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然后快速地拿起手里的剪刀,将它挑进我的篮中。但有的就长得比较模糊了,这些具有迷惑性的野菜会让我十分纠结。如果此时奶奶在离我不远处,我便会大喊让她前来辨认一下,如果不在,我就干脆直接挑起来抓在手中。往往到结束的时候,我的篮子里只有薄薄一层刚铺满底,其中还有一小半太老的野菜会在最后挑拣时被丢掉,然而我的手中却抓着满满一大把。虽然这里面很多是不能吃的品种,但我依旧会觉得自豪,一路握在手中,向人炫耀我的战果。
后面制作的步骤,十来岁的我就不再参与了,顶多在包馄饨时被喊过去帮忙,又在捏了几个软塌塌的小馄饨后被赶走。野菜馄饨的鲜美留在了那时候,在冷冽的冬日里,一家人围在一起,温暖的灯光衬着碗里升腾而起的热气,成为记忆中难以忘却的温馨时刻。
印象中都是在冬天去挑野菜,或者是乍暖还寒的初春。此刻田野里其实已经枯寂了,凋敝的大地上冒出头的绿只有各种坚韧不拔的野菜。夏侯湛所作的《荠赋》中这样说:“见芳荠之时生,被畦畴而独繁。钻重冰而挺茂,蒙严霜以发鲜。”野菜其实也是生命不息的代名词,虽然渺小但是依旧抵御寒冬,在大地上野蛮生长着,怎么不能算是一种独特的风流呢?
上周从图书馆里出来,去学校食堂吃了一份荠菜馄饨,和记忆中的味道实在没法比,不免生出了想念。只是如今乡下的家被重新规划后,许多曾经长野菜的地方已经被浇成了水泥路,大地上也愈来愈少能见到野菜的身影了,这一碗野菜馄饨似乎也只能留在记忆里鲜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