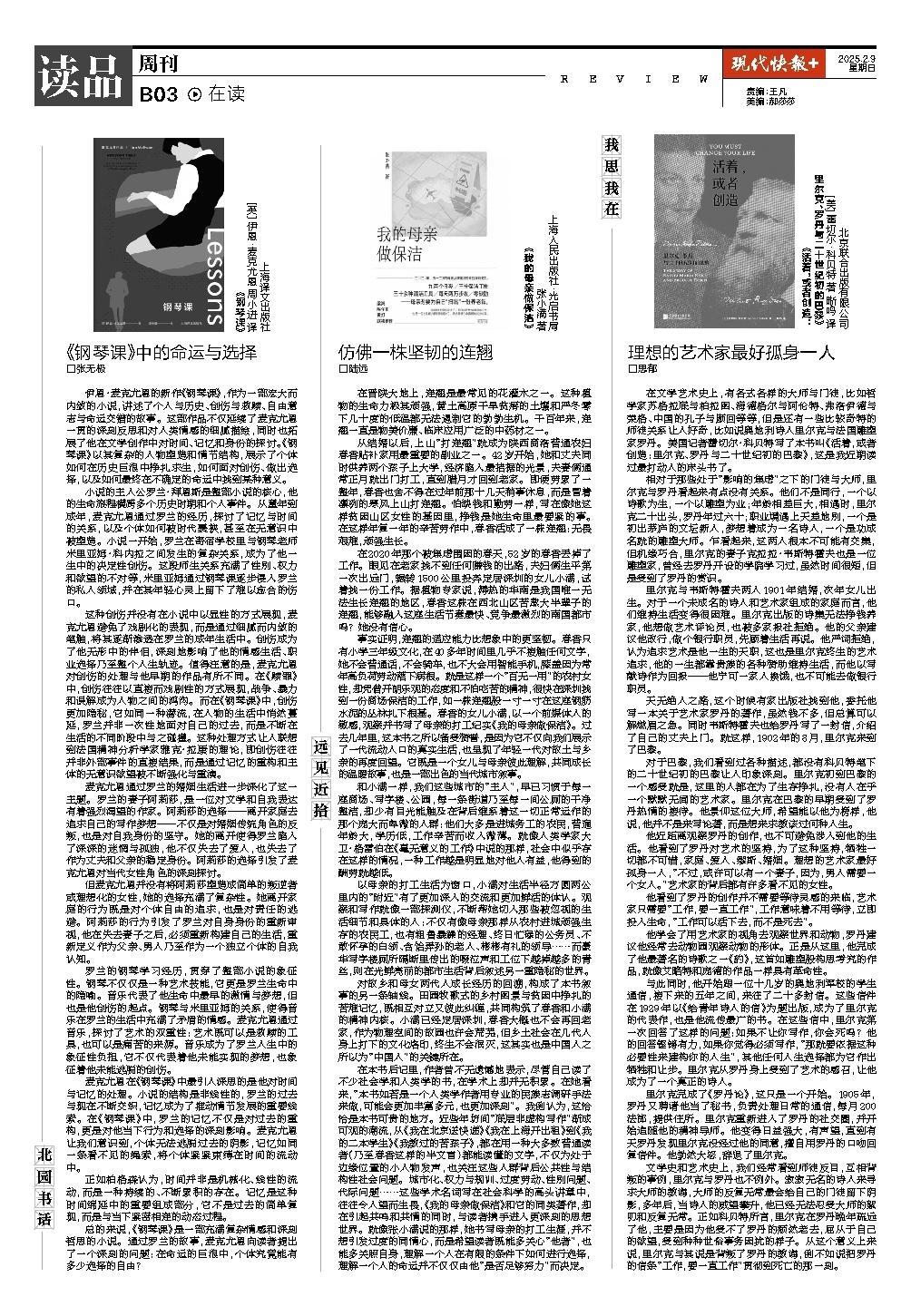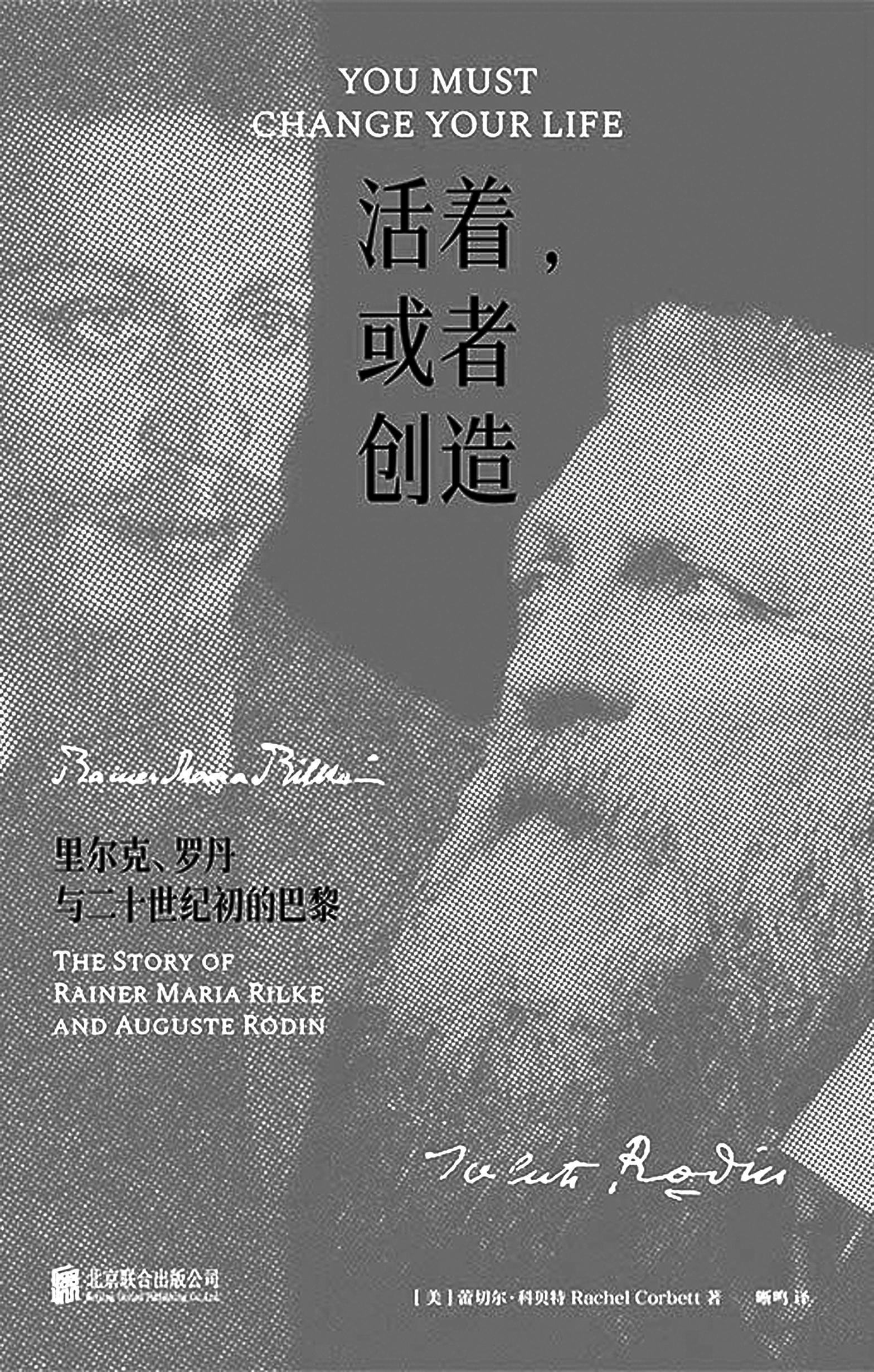□思郁
在文学艺术史上,有各式各样的大师与门徒,比如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柏拉图、海德格尔与阿伦特、弗洛伊德与荣格、中国的孔子与颜回等等,但是还有一些比较奇特的师徒关系让人好奇,比如说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与法国雕塑家罗丹。美国记者蕾切尔·科贝特写了本书叫《活着,或者创造:里尔克、罗丹与二十世纪初的巴黎》,这是我近期读过最打动人的床头书了。
相对于那些处于“影响的焦虑”之下的门徒与大师,里尔克与罗丹看起来有点没有关系。他们不是同行,一个以诗歌为生,一个以雕塑为业;年龄相差巨大,相遇时,里尔克二十出头,罗丹年过六十;职业境遇上天差地别,一个是初出茅庐的文坛新人,梦想着成为一名诗人,一个是功成名就的雕塑大师。乍看起来,这两人根本不可能有交集,但机缘巧合,里尔克的妻子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也是一位雕塑家,曾经去罗丹开设的学院学习过,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受到了罗丹的赏识。
里尔克与韦斯特霍夫两人1901年结婚,次年女儿出生。对于一个未成名的诗人和艺术家组成的家庭而言,他们维持生活变得很困难。里尔克出版的诗集无法挣钱养家,他想做艺术评论员,也被多家报社拒绝。他的父亲建议他改行,做个银行职员,先顾着生活再说。他严词拒绝,认为追求艺术是他一生的天职,这也是里尔克终生的艺术追求,他的一生都靠贵族的各种赞助维持生活,而他以写献诗作为回报——他宁可一家人挨饿,也不可能去做银行职员。
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时候有家出版社找到他,委托他写一本关于艺术家罗丹的著作,虽然钱不多,但总算可以解燃眉之急。同时韦斯特霍夫也给罗丹写了一封信,介绍了自己的丈夫上门。就这样,1902年的8月,里尔克来到了巴黎。
对于巴黎,我们看到过各种描述,都没有科贝特笔下的二十世纪初的巴黎让人印象深刻。里尔克初到巴黎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的人都在为了生存挣扎,没有人在乎一个默默无闻的艺术家。里尔克在巴黎的早期受到了罗丹热情的接待。他景仰这位大师,希望能以他为榜样,他说,他并不是来写论著,而是想来求教该过何种人生。
他近距离观察罗丹的创作,也不可避免涉入到他的生活。他看到了罗丹对艺术的坚持,为了这种坚持,牺牲一切都不可惜,家庭、爱人、缪斯、婚姻。理想的艺术家最好孤身一人,“不过,或许可以有一个妻子,因为,男人需要一个女人。”艺术家的背后都有许多看不见的女性。
他看到了罗丹的创作并不需要等待灵感的来临,艺术家只需要“工作,要一直工作”,工作意味着不用等待,立即投入生命,“工作可以活下去,而不是死去”。
他学会了用艺术家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和动物,罗丹建议他经常去动物园观察动物的形体。正是从这里,他完成了他最著名的诗歌之一《豹》,这首如雕塑般构思考究的作品,就像艾略特和庞德的作品一样具有革命性。
与此同时,他开始跟一位十几岁的奥地利军校的学生通信,接下来的五年之间,来往了二十多封信。这些信件在1929年以《给青年诗人的信》为题出版,成为了里尔克的代表作,也是他流传最广的书。在这些信中,里尔克第一次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不让你写作,你会死吗?他的回答铿锵有力,如果你觉得必须写作,“那就要依据这种必要性来建构你的人生”,其他任何人生选择都为它作出牺牲和让步。里尔克从罗丹身上受到了艺术的感召,让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诗人。
里尔克完成了《罗丹论》,这只是一个开始。1905年,罗丹又聘请他当了秘书,负责处理日常的通信,每月200法郎,提供住所。里尔克重新进入了罗丹的社交圈,并开始追随他的精神导师。他变得日益强大,有声望,直到有天罗丹发现里尔克没经过他的同意,擅自用罗丹的口吻回复信件。他勃然大怒,辞退了里尔克。
文学史和艺术史上,我们经常看到师徒反目,互相背叛的事例,里尔克与罗丹也不例外。寂寂无名的诗人来寻求大师的教诲,大师的反复无常最会给自己的门徒留下阴影,多年后,当诗人的威望攀升,他已经无法忍受大师的絮叨和反复无常。正如科贝特所言,里尔克在罗丹晚年疏远了他,主要是因为他受不了罗丹的颓然老去,屈从于自己的欲望,受到种种世俗事务困扰的样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里尔克与其说是背叛了罗丹的教诲,倒不如说把罗丹的信条“工作,要一直工作”贯彻到死亡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