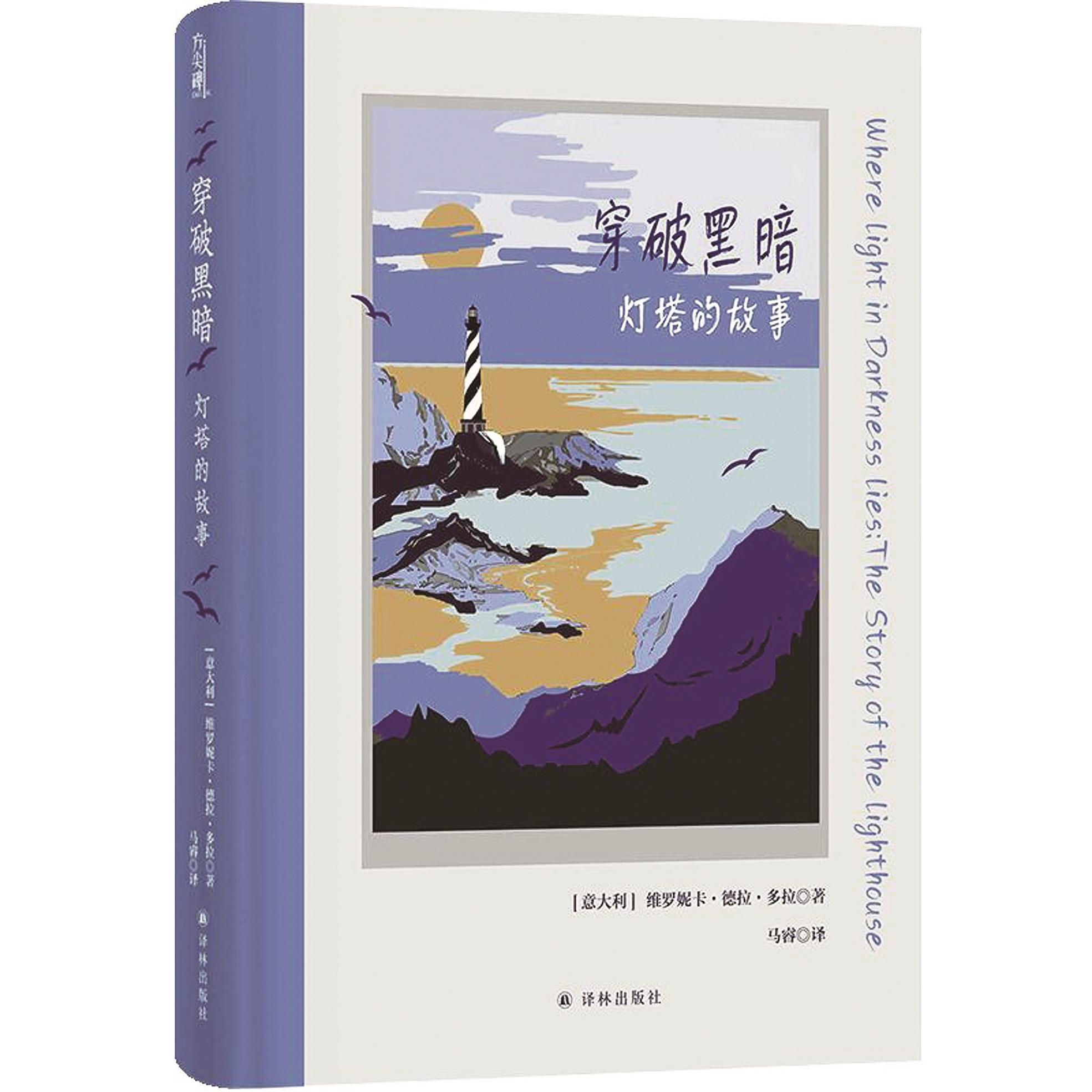□马睿
2022年10月底,我接受了译林出版社编辑许丹的委托,翻译一本关于灯塔的小书。书还没有读,翻译也还没开始,我碰巧有个假期,南下去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跟高中好友相聚。那个周末我们从波特兰市开车向西到纽波特海滨,在一条经典的游玩线路上,我与亚基纳角灯塔(Yaquina Head Light)不期而遇。从一英里步道外的停车场一下车,我的视线便再也离不开那座灯塔。在湛蓝的天空下,四周是初冬泛黄无人打理的野草,它优雅得像《蒂凡尼的早餐》中身穿小黑裙的赫本,白色圆锥体上端是黑顶的灯室,下面盖着一间简朴的守护人住所,也只有黑白两色。据说在初冬的西海岸,那天的碧空如洗并不多见,海、天、岬角和灯塔在我眼前构成了一幅绝佳的画作,无一笔不精,无一色不妙。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有意识地观看灯塔,回想起来,最神奇的却是那股像磁铁一般的魔力,我的目光和脚步被灯塔吸引着,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朝它走过去,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寂静而模糊了。
由于这个美丽的巧合,其后翻译《穿破黑暗:灯塔的故事》的那几个月就一点一点地为我揭开了这个谜底:那股吸引我走向灯塔的魔力从何而来?静谧沉默的灯塔,何以对人类的思想和想象有着如此难以摆脱的吸引力?这是一部优美的人文主义地理学读本,意大利地理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维罗妮卡·德拉·多拉为我们呈现了一部灯塔小传,而这本书的结构本身,就直观地说明了何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它只在短短13页篇幅的“附录”中,用(不无枯燥的)术语和示意图阐述了“灯塔的构成与运作方式”,它的正文部分探讨的,并非灯塔这种建筑本身的构造和功能、它的光学和声学原理和运作,或者世界各国建设灯塔网络的历史和现状,而是自始至终都在追寻灯塔的意义,它描述的是在全人类的意识、记忆和文艺作品中作为强有力的象征和隐喻的灯塔,“心灵的灯塔”。
何以如此?为什么在众多承载着人文历史的建筑中,例如佛塔、教堂、歌剧院、博物馆等等,唯独作为概念的灯塔有着这样普世的神秘吸引力和象征意义?本书揭示的答案之一是,灯塔作为一种阈限建筑,本身构成了一种矛盾修辞。在不大久远的过去,航海还充满危险,连不可一世的泰坦尼克号海难也不过是一百多年前的往事,而探索海洋的征程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可以想象,在作为陆生生物的人类的内心深处和远古记忆中,海洋酝酿着怎样的险恶。位于“陆止于斯,海始于斯”的边缘地带的灯塔,最初的功能是为航行的水手提供光明和指引,但这本身便是黑暗和危险的征兆,水手们最需要灯塔的时候,恰恰是晦暗无光、怒海翻波或雾锁重洋的时候,一不小心便樯倾楫摧、葬身鱼腹。灯塔的历史,就是人类克服困难远征海洋的历史,但“无论是为水手还是为飞行员导航,灯塔存在的理由及其用途就在于它的不可移动性”。在喜怒无常的海面上,在前路未卜的旅程中,灯塔是固定和静止的锚点。在人类心向远方的追索中,灯塔始终坚守在原地,为远航之人执起那盏微光,“它们在地形上的坚守看似与机动性相抗衡,但也正是它们的坚守实现了这种机动性”。在浩瀚的海平面和周遭海岸,灯塔这种垂直高耸的建筑结构使它们在醒目的同时也尤为孤单,“加上它们精致的比例和清晰的线条,这些被海浪冲刷的孤寂建筑物有一种神秘而荒凉的美感,”然而从它被发明出来的第一天起,灯塔的功能就是与海上的水手取得联系,它向海面发出信号,以确保水手能够接收到信号并获得指引。后来随着海岸灯塔数目的增加,灯塔也成为海上人员和物质流动的一部分。灯塔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然而它的存在本身恰是人类意识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作者引用英国历史学家R.G.格兰特指出,“灯塔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不可一世的印记,恰恰相反,它们反映了人类在面对海洋和风暴等自然力量时,总是如此身单力薄。”在气候变化灾难频发的当今,这最后一点尤其在能我们的内心中引发巨大共鸣。光明与幽暗、安全与危险、坚守与远行、孤寂与联结,人类自身的伟大与脆弱,灯塔自问世之初就在这些相对立的观念之间力图实现岌岌可危的平衡,这无疑赋予了灯塔一种存在的美感和神秘感。
正因为灯塔这些矛盾而神秘的特质,它也成为各类文艺作品最热爱的主题和主角之一。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曾写下“爱是亘古长明的塔灯,它定睛望着风暴却兀不为动”的诗行。而灯塔作为戏剧发生地和光谱相交处的浪漫主义建构,常常在现代文学和电影中成为内心探索之旅的舞台,正如本书作者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所说,“电影界有一条安全的经验法则,那就是灯塔里准没什么好事发生。”这本《穿破黑暗:灯塔的故事》用九十多幅精美印刷的图片,展示了大量文艺作品中的灯塔,包括油画和水彩画作、摄影作品、电影海报、书籍插图、明信片乃至广告宣传片,对我这位大部分时间都在文字的迷宫中寻幽探胜的译者,也是巨大的享受。如此大量的文艺作品以灯塔为主题,既反映出灯塔在人类集体记忆和想象中的独特魅力,它们本身也强化了这一点。翻译完这本书后,我又拿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到灯塔去》重读,发现小说文字中暗藏的大量灯塔意象和象征意义居然是以前阅读时没有察觉到的,即便当年作为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曾经为了写学期论文而精读过好几遍原著。我想,阅读这部灯塔小传的成就感之一,就是下一次在小说电影或艺术作品中见到灯塔,我们会洞悉那象征性的画面或主题所自何来,也会让它轻轻地触动一根心弦:啊,原来你也在这里。
《穿破黑暗:灯塔的故事》翻译结束之后的那个月,我带父母去温哥华旅行。在我去过很多次的斯坦利公园,我和父母一边聊天,一边沿公园里的海墙漫步。这时,我第一次发现,这里居然有一座灯塔!四边形的布洛克顿角灯塔仅有十米高,塔体呈白色,中段有一圈粉红色饰边,顶上是一个方形露台和红色的八角形灯室。游人既可以从下面仰视它,也可以沿楼梯走到它背后的入口处。布洛克顿角灯塔如今位于温哥华的中心地带,游客最多的打卡地,但在不大遥远的过去,它也曾是偏远海角的守护者。不知道是它那居家而毫不张扬的色彩和气质,还是因为这一次是跟家人在一起,小小的布洛克顿角灯塔给我的感觉不是摄人心魄的气势,而要温柔和温暖得多。像世间所有的灯塔一样,它照亮的是一段回家的路。
(作者系《穿破黑暗:灯塔的故事》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