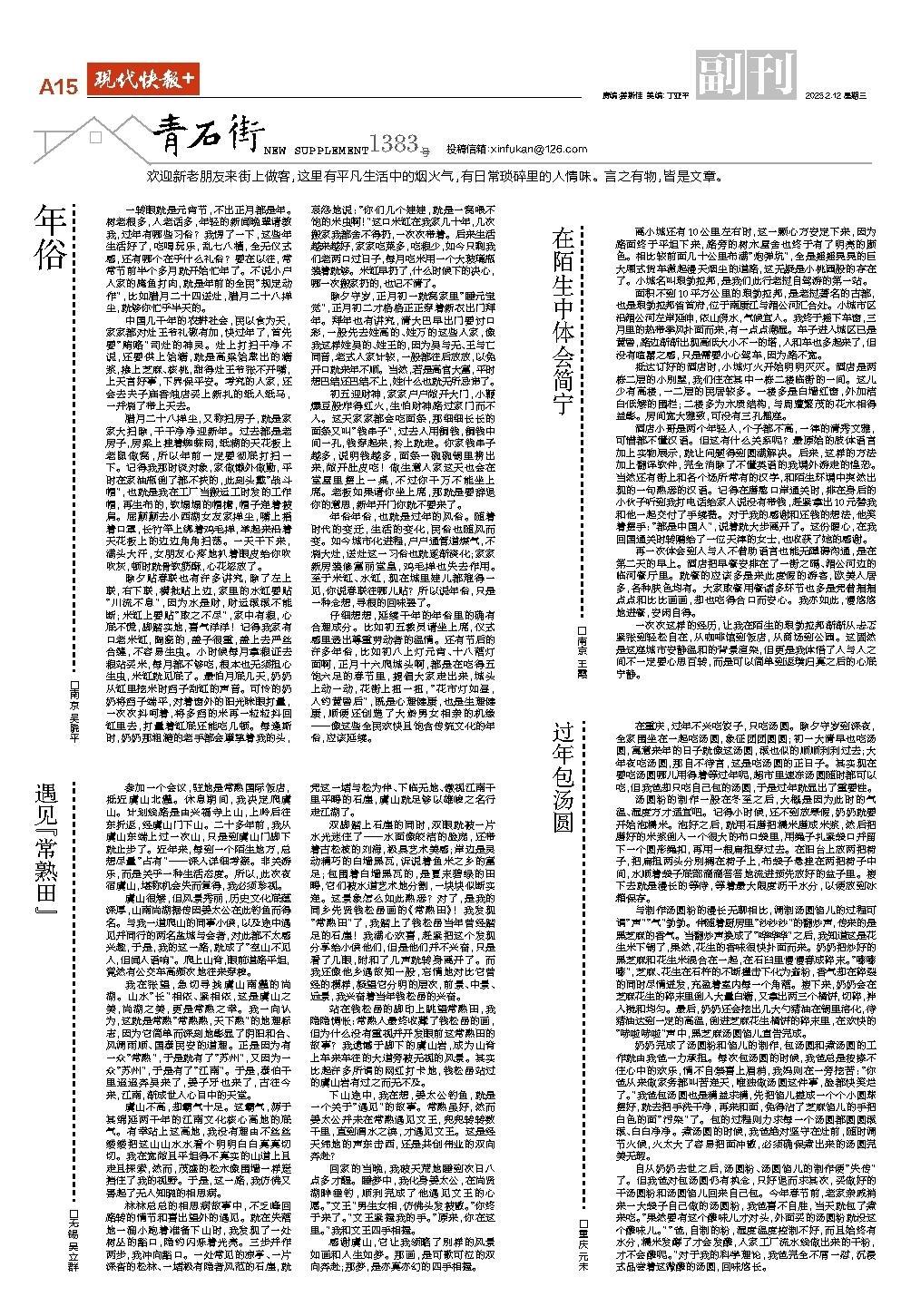□南京 吴晓平
一转眼就是元宵节,不出正月都是年。树老根多,人老话多,年轻的新闻晚辈请教我,过年有哪些习俗?我愣了一下,这些年生活好了,吃喝玩乐,乱七八糟,全无仪式感,还有哪个在乎什么礼俗?要在以往,常常节前半个多月就开始忙年了。不说小户人家的腌鱼打肉,就是年前的全民“规定动作”,比如腊月二十四送灶,腊月二十八掸尘,就够你忙乎半天的。
中国几千年的农耕社会,民以食为天,家家都对灶王爷礼敬有加,快过年了,首先要“贿赂”司灶的神灵。灶上打扫干净不说,还要供上饴糖,就是高粱饴熬出的糖浆,掺上芝麻、核桃,甜得灶王爷张不开嘴,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考究的人家,还会去夫子庙香烛店买上新扎的纸人纸马,一并烧了带上天去。
腊月二十八掸尘,又称扫房子,就是家家大扫除,干干净净迎新年。过去都是老房子,房梁上挂着蜘蛛网,纸糊的天花板上老鼠做窝,所以年前一定要彻底打扫一下。记得我那时谈对象,家做懒外做勤,平时在家油瓶倒了都不扶的,此刻头戴“战斗帽”,也就是我在工厂当搬运工时发的工作帽,再生布的,软塌塌的帽檐,帽子连着披肩。屁颠颠去小西湖女友家掸尘,嘴上捂着口罩,长竹竿上绑着鸡毛掸,举起来沿着天花板上的边边角角扫荡。一天干下来,满头大汗,女朋友心疼地扒着眼皮给你吹吹灰,顿时就骨软筋酥,心花怒放了。
除夕贴春联也有许多讲究,除了左上联,右下联,横批贴上边,家里的水缸要贴“川流不息”,因为水是财,财运滚滚不能断;米缸上要贴“取之不尽”,家中有粮,心底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记得我家有口老米缸,陶瓷的,盖子很重,盖上去严丝合缝,不容易生虫。小时候每月拿粮证去粮站买米,每月都不够吃,根本也无须担心生虫,米缸就见底了。最怕月底几天,奶奶从缸里挖米时舀子刮缸的声音。可怜的奶奶将舀子端平,对着窗外的阳光眯眼打量,一次次抖呵着,将多舀的米再一粒粒抖回缸里去,打量着缸底还能吃几顿。每逢斯时,奶奶那粗糙的老手都会摩挲着我的头,哀怨地说:“你们几个娃娃,就是一窝喂不饱的米虫啊!”这口米缸在我家几十年,几次搬家我都舍不得扔,一次次带着。后来生活越来越好,家家吃菜多,吃粮少,如今只剩我们老两口过日子,每月吃米用一个大玻璃瓶装着就够。米缸早扔了,什么时候下的决心,哪一次搬家扔的,也记不清了。
除夕守岁,正月初一就窝家里“睡元宝觉”,正月初二才格格正正穿着新衣出门拜年。拜年也有讲究,清大巴早出门要讨口彩,一般先去姓高的、姓万的这些人家,像我这样姓吴的、姓王的,因为吴与无、王与亡同音,老式人家计较,一般都往后放放,以免开口就来年不顺。当然,若是高官大富,平时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姓什么也就无所忌讳了。
初五迎财神,家家户户敞开大门,小鞭爆豆般炸得红火,生怕财神路过家门而不入。这天家家都会吃面条,那细细长长的面条又叫“钱串子”,过去人用铜钱,铜钱中间一孔,钱穿起来,拎上就走。你家钱串子越多,说明钱越多,面条一碗碗锅里捞出来,敞开肚皮吃!做生意人家这天也会在堂屋里摆上一桌,不过你千万不能坐上席。老板如果请你坐上席,那就是要辞退你的意思,新年开门你就不要来了。
年俗年俗,也就是过年的风俗。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的变化,民俗也随风而变。如今城市化进程,户户通管道煤气,不烧大灶,送灶这一习俗也就逐渐淡化;家家新房装修富丽堂皇,鸡毛掸也失去作用。至于米缸、水缸,现在城里娃儿都难得一见,你说春联往哪儿贴?所以说年俗,只是一种念想,寻根的回味罢了。
仔细想想,延续千年的年俗里的确有合理成分。比如初五裁员请坐上席,仪式感里透出尊重劳动者的温情。还有节后的许多年俗,比如初八上灯元宵、十八落灯面啊,正月十六爬城头啊,都是在吃得五饱六足的春节里,提倡大家走出来,城头上动一动,花街上扭一扭,“花市灯如昼,人约黄昏后”,既是心理健康,也是生理健康,顺便还创造了大龄男女相亲的机缘——像这些全民欢快且饱含传统文化的年俗,应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