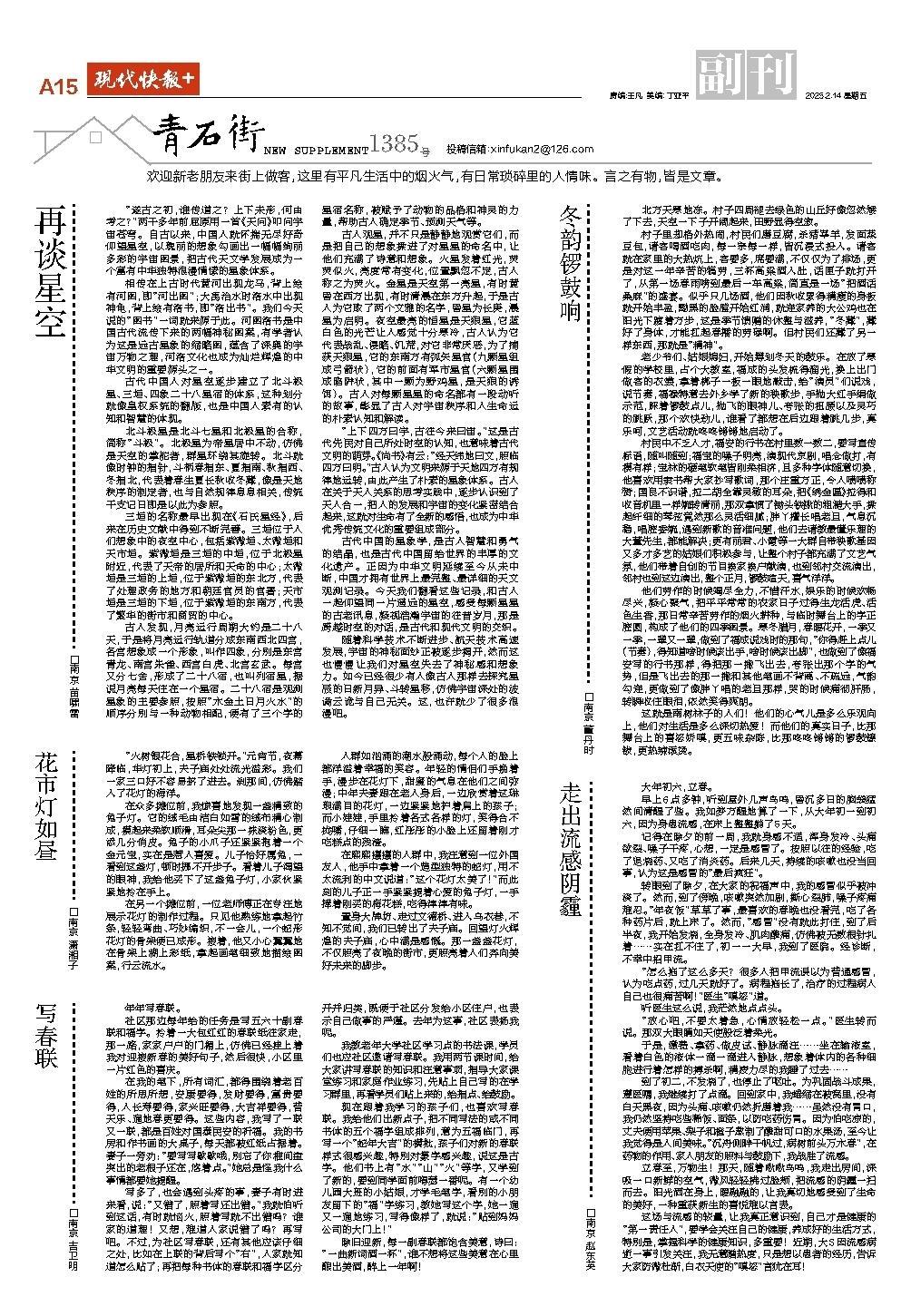□南京 董丹时
北方天寒地冻。村子四周褪去绿色的山丘好像忽然矮了下去,天空一下子开阔起来,田野显得空寂。
村子里却格外热闹,村民们磨豆腐,杀猪宰羊,发面蒸豆包,请客喝酒吃肉,每一宗每一样,皆沉浸式投入。请客就在家里的大热炕上,客要多,席要满,不仅仅为了排场,更是对这一年辛苦的犒劳,三杯高粱酒入肚,话匣子就打开了,从第一场春雨唠到最后一车高粱,简直是一场“把酒话桑麻”的盛宴。似乎只几场酒,他们因秋收累得精瘦的身板就开始丰盈,黝黑的脸膛开始红润,就连家养的大公鸡也在阳光下踱着方步,这是季节馈赠的休整与滋养,“冬藏”,藏好了身体,才能扛起春播的劳碌啊。但村民们还藏了另一样东西,那就是“精神”。
老少爷们、姑娘媳妇,开始筹划冬天的鼓乐。在放了寒假的学校里,占个大教室,福成的头发梳得溜光,换上出门做客的衣裳,拿着梆子一板一眼地敲击,给“演员”们说戏,说节奏,福禄特意去外乡学了新的秧歌步,手抛大红手绢做示范,踩着锣鼓点儿,抛飞的眼神儿、夸张的扭腰以及灵巧的跳跃,那个欢快劲儿,谁看了都想在后边跟着跳几步,真乐呵,文艺活动就咚咚锵锵地启动了。
村民中不乏人才,福安的行书在村里数一数二,要写宣传标语,随叫随到;福宝的嗓子明亮,演现代京剧,唱念做打,有模有样;宝林的硬笔软笔皆刚柔相济,且多种字体随意切换,他喜欢用隶书帮大家抄写歌词,那个庄重方正,令人啧啧称赞;国良不识谱,拉二胡全靠灵敏的耳朵,把《绣金匾》拉得和收音机里一样婉转清丽,那双拿惯了锄头铁锹的粗糙大手,揉起纤细的琴弦竟然那么灵活细腻;胖丫擅长唱老旦,气息沉稳,唱腔委婉,遇到新歌的音准问题,他们去请教最懂乐理的大董先生,都能解决;更有丽君、小霞等一大群自带秧歌基因又多才多艺的姑娘们积极参与,让整个村子都充满了文艺气氛,他们带着自创的节目挨家挨户献演,也到邻村交流演出,邻村也到这边演出,整个正月,锣鼓喧天,喜气洋洋。
他们劳作的时候竭尽全力,不惜汗水,娱乐的时候欢畅尽兴,凝心聚气,把平平常常的农家日子过得生龙活虎、活色生香,那日常辛苦劳作的烟火耕种,与临时舞台上的字正腔圆,构成了他们的四季图景。寒冬腊月,春暖花开,一季又一季,一辈又一辈,做到了福成说戏时的那句,“你得赶上点儿(节奏),得知道啥时候该出手,啥时候该出脚”,也做到了像福安写的行书那样,得把那一撇飞出去,夸张出那个字的气势,但是飞出去的那一撇和其他笔画不背离、不疏远,气韵勾连,更做到了像胖丫唱的老旦那样,哭的时候痛彻肝肠,转瞬收住眼泪,依然笑得爽朗。
这就是南树林子的人们!他们的心气儿是多么乐观向上,他们对生活是多么深切热爱!而他们的真实日子,比那舞台上的喜怒娇嗔,更五味杂陈,比那咚咚锵锵的锣鼓镲钹,更热辣滚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