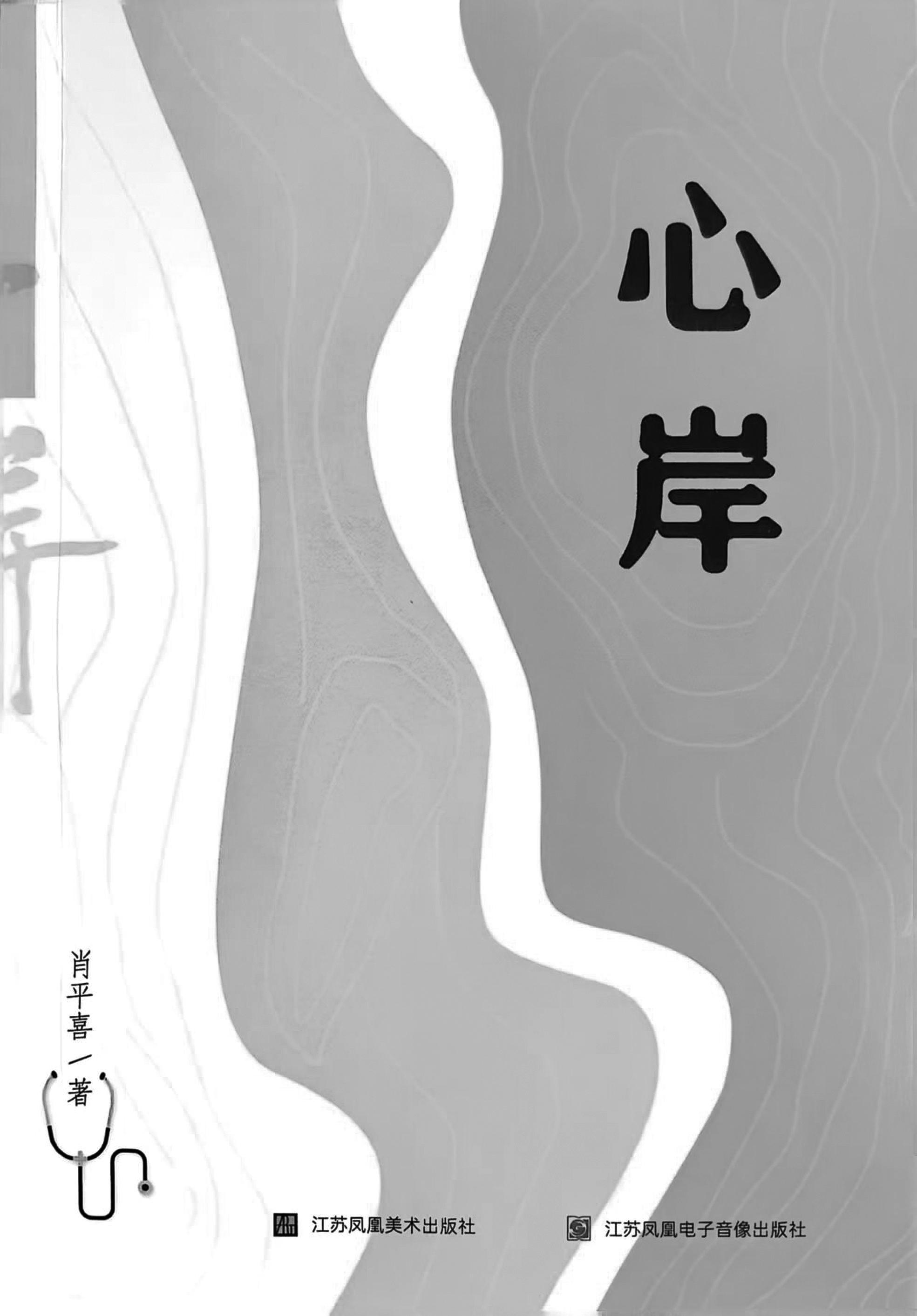□张德强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医生的诗集,《心岸》这一书名暗示了水的存在。诗人说:“有/一种幽独/植根于亘古的经络与血/如同伤口朝天而开/临水而居”(《致L君》),在这里,水的意象意味着一种抽离出红尘的凝视,一种面对生命的沉思与平衡。
韩东说,当一个人开始写作时,“关键是对谁说话,想象的或实际上的读者是谁?”(《五万言》)诗人此刻所面对的,并不是病人,而是生命之河的另一岸,又非我们平日所说的隐喻超越性的彼岸,而是此岸的一部分,是用以规定此岸的、日常以外的世界一侧。这便是诗人诉说的对象。时间在这几十首诗里占据了隐然却显要的位置,时间规定起不断的回忆、回归与回溯,往事、乡土、友人及爱情不断浮现又消隐。面对时间,诗人说:“你像个孩子/怅然若失/他有他的归宿/她有她的去处/剩下你和空屋子/满载着孤独”(《每当曲终人散时》),他不回避情绪,感伤地咀嚼人到中年的迷惘:“我泪流满面/我已经站在路的中间/人生过半”(《2019中秋写给你们》),又不无冷静面对人生得失的省思:“是一时的赢/还是一世的赢/是一个人的赢/还是一队人的赢/是躯壳的疲惫/还是心的宁定”(《余生》)。
于是,“心岸”沿途的浮光掠影,都在诗人手中触笔成歌,在异国遇到的鸟儿,让他想起了古老的中国意象:“它们 多好/点缀着维也纳美丽的秋/也点缀着无语的心/五十年后的早晨 依然年轻”(《维也纳双飞鸟》)。他将对于爱情深沉的怀念融入梦中:“她还是误闯进我的梦乡/我张开早已铺就的网/再也不想扑个空”(《五十年后》)。我们想象,在诗的国度里,在心的另一岸,在深夜里,诗人结束了一天工作,终于释放自己,忍不住写下这样的诗句:“我是一个藏不住笑容的孩子/最怕见到婴儿、飞鸟、云层和阳光/风中幽默的乐观的人们/和雨过天晴的景象”(《藏不住》)。这首诗里最意味深长的恐怕是“藏”字,诗意躲藏在白天的繁忙、目睹的伤痛、医者的仁心与无奈中,白日里他必须是医学权威、是病患的慰藉与源泉,只有在黑夜里,那被藏住的才无须隐藏,才可被释放。
诗人感性、敏锐,又善于将其捕捉为象征,于是,便有这样情绪与无意识交织的佳句:“暮春的白昼囚禁了我/在泥水的喧嚣中萎靡/当昏暗拉上窗帘”(《五月》);偶然的思绪日益积累为浓缩的苦涩:“却找不到臆想中的对焦/于是你后退到暗箱/却依然/被热切的目光灼痛”(《胶卷》);诗人尤其钟爱晨光,他在黄昏时也会回想初升之阳光,将其熔炼为他者的沉思:“你把黄昏咀嚼了千遍/一只眼的余光/却瞟向了黎明”(《晨光系列之——浮草》)。
诗人对于现代以来的诗歌传统显然有着相当了解,他会在诗中与海子对话,会将新月派的整饬凝练融为音韵铿锵:“我看到灰褐的夜光/作别那遥远的天河/我听到雄浑的低吼/把闷雷和骤雨穿透”(《无题——写于扬子江畔》)。也许,最具匠心的还在于那些较长的作品,它们体现出一种医者/诗人身份交织中对生命复杂的态度。在《晨光系列之——对峙》,诗人用“对峙”一词表达出积极生活的生命勇气,连续7个“藏起”编织出的头韵,交叠起坚实的生命态度。还有《半梦半醒之间》中的苦涩与温情,《2016第一场雪》里的希冀和怅惘,《先尝》里的感恩与低徊。在这些诗里,诗人实现了一种朴素与情思交替萦绕的力量。
我们想起对于另一位医生/作家的评价,他“善于把瞬息即逝的创作忧虑保存在自己心中,他善于把热情和沉思的时刻延长到整个一生”([俄]格罗莫夫《契诃夫传》),《心岸》的作者方才“站在路的中间”,愿他一直葆有对生命的虔诚与激情,继续将白日“藏起”的忧郁和热情寄托在诗中并“延长到整个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