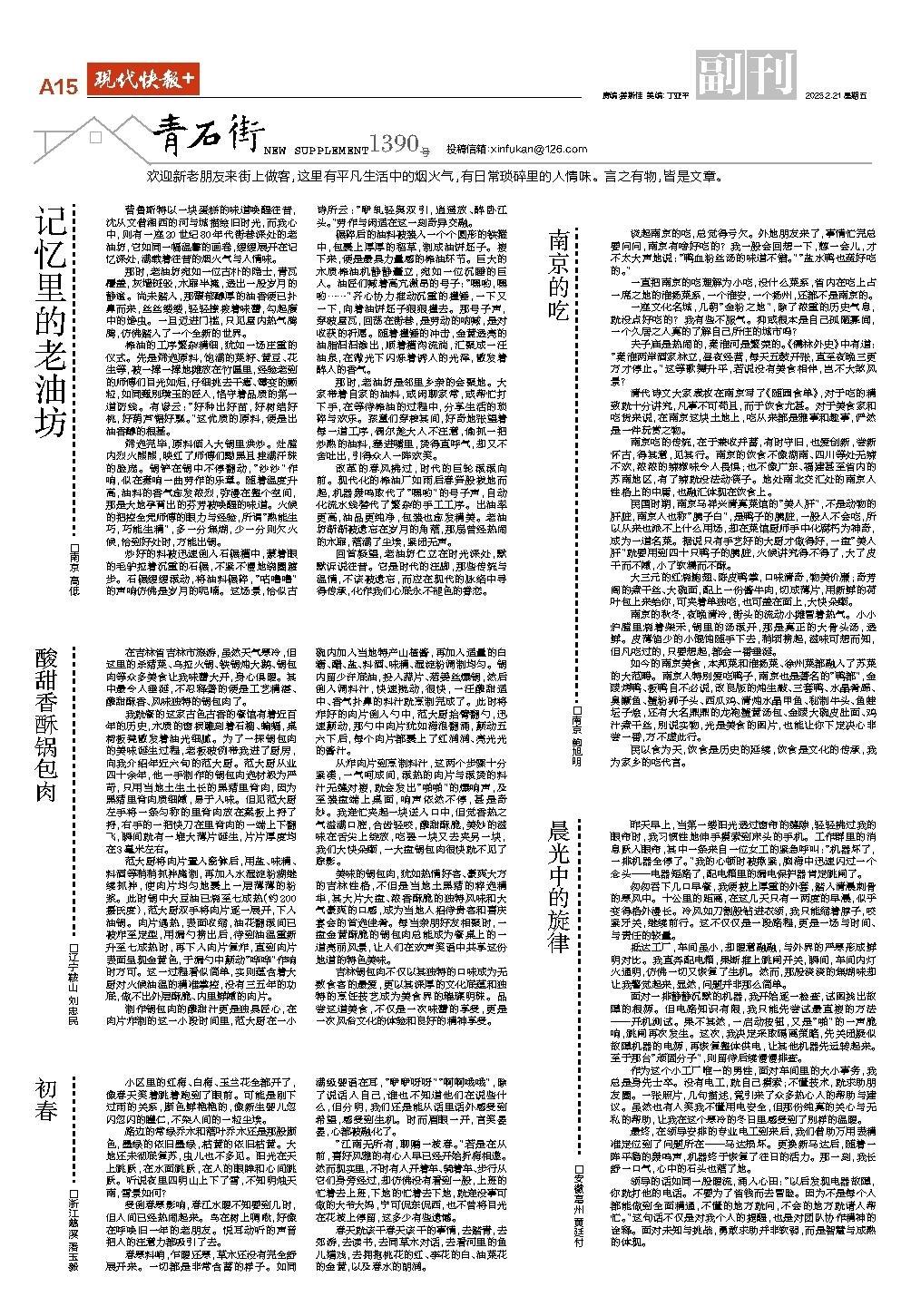□南京 鲍旭明
谈起南京的吃,总觉得亏欠。外地朋友来了,事情忙完总要问问,南京有啥好吃的?我一般会回想一下,憋一会儿,才不太大声地说:“鸭血粉丝汤的味道不错。”“盐水鸭也蛮好吃的。”
一直把南京的吃理解为小吃,没什么菜系,省内在吃上占一席之地的淮扬菜系,一个淮安,一个扬州,还都不是南京的。
一座文化名城,几朝“金粉之地”,除了浓重的历史气息,就没点好吃的?我有些不服气。抑或根本是自己孤陋寡闻,一个久居之人真的了解自己所住的城市吗?
夫子庙是热闹的,秦淮河是繁荣的。《儒林外史》中有道:“秦淮两岸酒家林立,昼夜经营,每天五鼓开张,直至夜晚三更方才停止。”这等歌舞升平,若说没有美食相伴,岂不大煞风景?
清代诗文大家袁枚在南京写了《随园食单》,对于吃的精致就十分讲究,凡事不可苟且,而于饮食尤甚。对于美食家和吃货来说,在南京这块土地上,吃从来都是雅事和趣事,俨然是一件玩赏之物。
南京吃的传统,在于兼收并蓄,有时守旧,也爱创新,尝新怀古,得其意,见其行。南京的饮食不像湖南、四川等处无辣不欢,浓浓的辣椒味令人畏惧;也不像广东、福建甚至省内的苏南地区,有了辣就没法动筷子。地处南北交汇处的南京人性格上的中庸,也融汇体现在饮食上。
民国时期,南京马祥兴清真菜馆的“美人肝”,不是动物的肝脏,南京人也称“胰子白”,是鸭子的胰脏,一般人不会吃,所以从来也派不上什么用场,却在菜馆厨师手中化腐朽为神奇,成为一道名菜。据说只有手艺好的大厨才做得好,一盘“美人肝”就要用到四十只鸭子的胰脏,火候讲究得不得了,大了皮干而不嫩,小了软糯而不酥。
大三元的红烧鲍翅、陈皮鸭掌,口味清奇,物美价廉;奇芳阁的煮干丝、大碗面,配上一份酱牛肉,切成薄片,用新鲜的荷叶包上来给你,可夹着单独吃,也可盖在面上,大快朵颐。
南京的秋冬,夜晚清冷,街头的流动小摊冒着热气。小小炉膛里烧着柴禾,锅里的汤滚开,那是真正的大骨头汤,透鲜。皮薄馅少的小馄饨随手下去,稍顷捞起,滋味可想而知,但凡吃过的,只要想起,都会一番垂涎。
如今的南京美食,本邦菜和淮扬菜、徐州菜都融入了苏菜的大范畴。南京人特别爱吃鸭子,南京也是著名的“鸭都”,金陵烤鸭、板鸭自不必说,改良版的炖生敲、三套鸭、水晶肴蹄、臭鳜鱼、蟹粉狮子头、西瓜鸡、清炖水晶甲鱼、秘制牛头、鱼蛙坛子烩,还有大名鼎鼎的龙袍蟹黄汤包、金陵大碗皮肚面、鸡汁煮干丝,别说实物,光是美食的图片,也能让你下定决心非尝一番,方不虚此行。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历史的延续,饮食是文化的传承,我为家乡的吃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