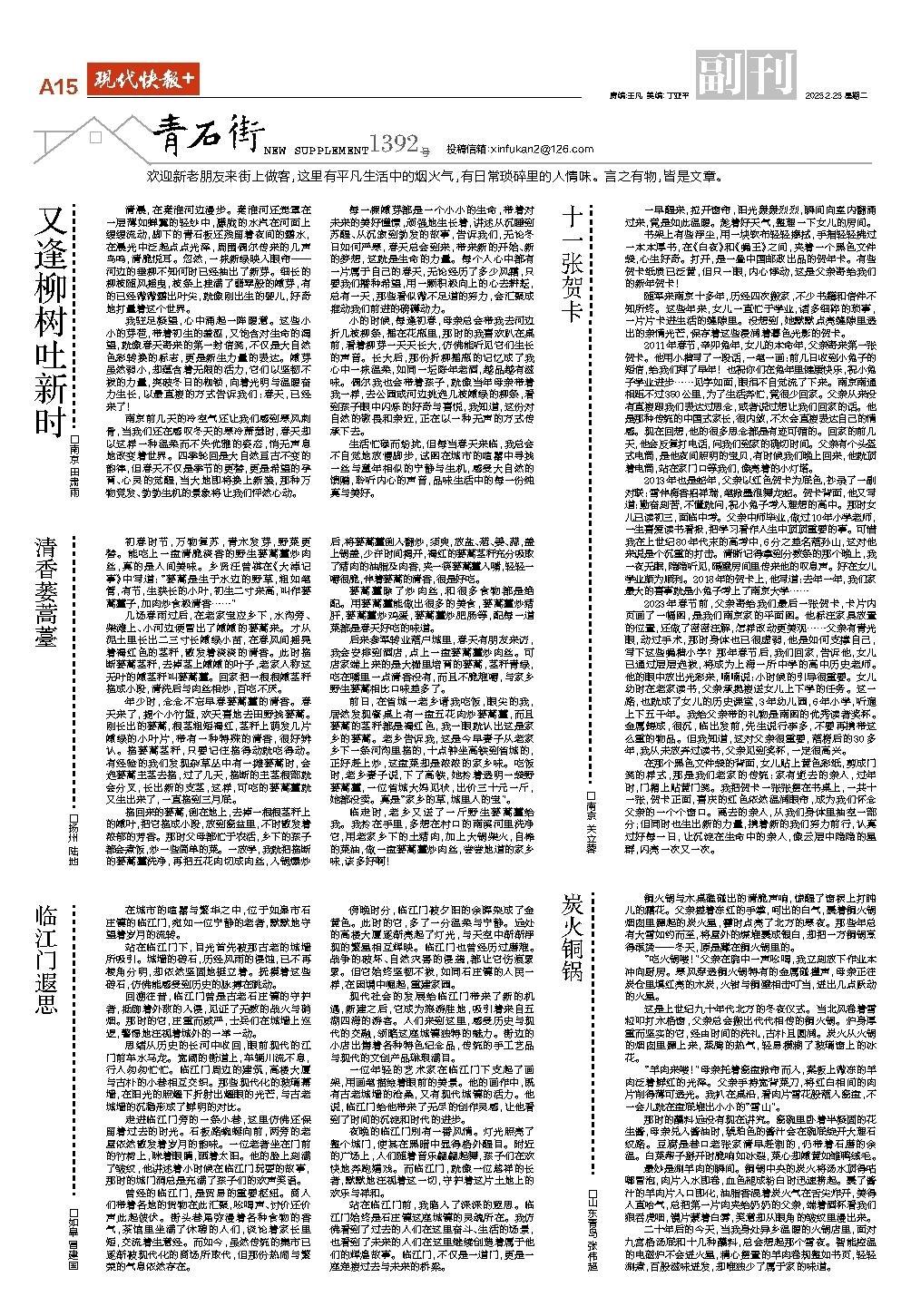□山东青岛 张伟超
铜火锅与木桌磕碰出的清脆声响,惊醒了窗棂上打盹儿的霜花。父亲搓着冻红的手掌,呵出的白气,裹着铜火锅烟囱里蹿起的炭火星,霎时点亮了北方的寒夜。那些年总有大雪如约而至,将屋外的煤堆裹成银白,却把一方铜锅烹得滚烫——冬天,原是藏在铜火锅里的。
“吃火锅喽!”父亲在院中一声吆喝,我立刻放下作业本冲向厨房。寒风穿透铜火锅特有的金属碰撞声,母亲正往炭仓里填红亮的木炭,火钳与铜壁相击叮当,迸出几点跃动的火星。
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北方的冬夜仪式。当北风卷着雪粒叩打木格窗,父亲总会搬出代代相传的铜火锅。炉身厚重而坚实的它,经由时间的洗礼,古朴且圆润。炭火从火锅的烟囱里蹿上来,蒸腾的热气,轻易模糊了玻璃窗上的冰花。
“羊肉来喽!”母亲托着瓷盘掀帘而入,案板上微冻的羊肉泛着鲜红的光泽。父亲手持宽背菜刀,将红白相间的肉片削得薄可透光。我扒在桌沿,看肉片雪花般落入瓷盘,不一会儿就在盘底堆出小小的“雪山”。
那时的蘸料远没有现在讲究。瓷碗里卧着半凝固的花生酱,母亲兑入酱油时,琥珀色的酱汁会在碗底绽开大理石纹路。豆腐是巷口老张家清早赶制的,仍带着石磨的余温。白菜帮子掰开时脆响如冰裂,菜心却嫩黄如雏鸭绒毛。
最妙是涮羊肉的瞬间。铜锅中央的炭火将汤水顶得咕嘟冒泡,肉片入水即卷,血色褪成粉白时迅速捞起。裹了酱汁的羊肉片入口即化,油脂香混着炭火气在舌尖炸开,美得人直哈气,总把第一片肉夹给奶奶的父亲,端着酒杯看我们狼吞虎咽,镜片蒙着白雾,笑意却从眼角的皱纹里漫出来。
二十年后的今天,当我身处异乡温暖的火锅店里,面对九宫格汤底和十几种蘸料,总会想起那个雪夜。智能控温的电磁炉不会迸火星,精心摆置的羊肉卷规整如书页,轻轻涮煮,百般滋味迸发,却唯独少了属于家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