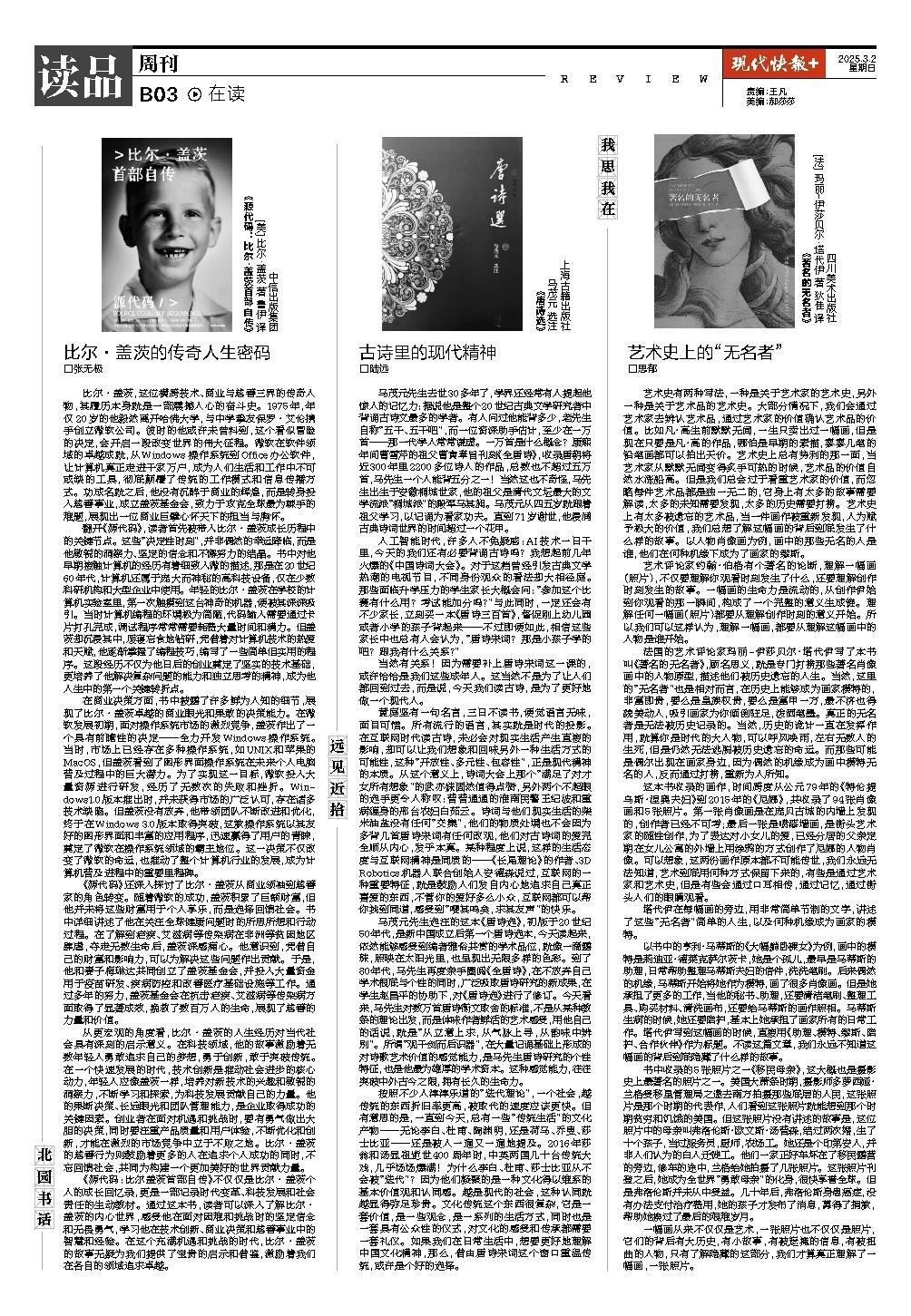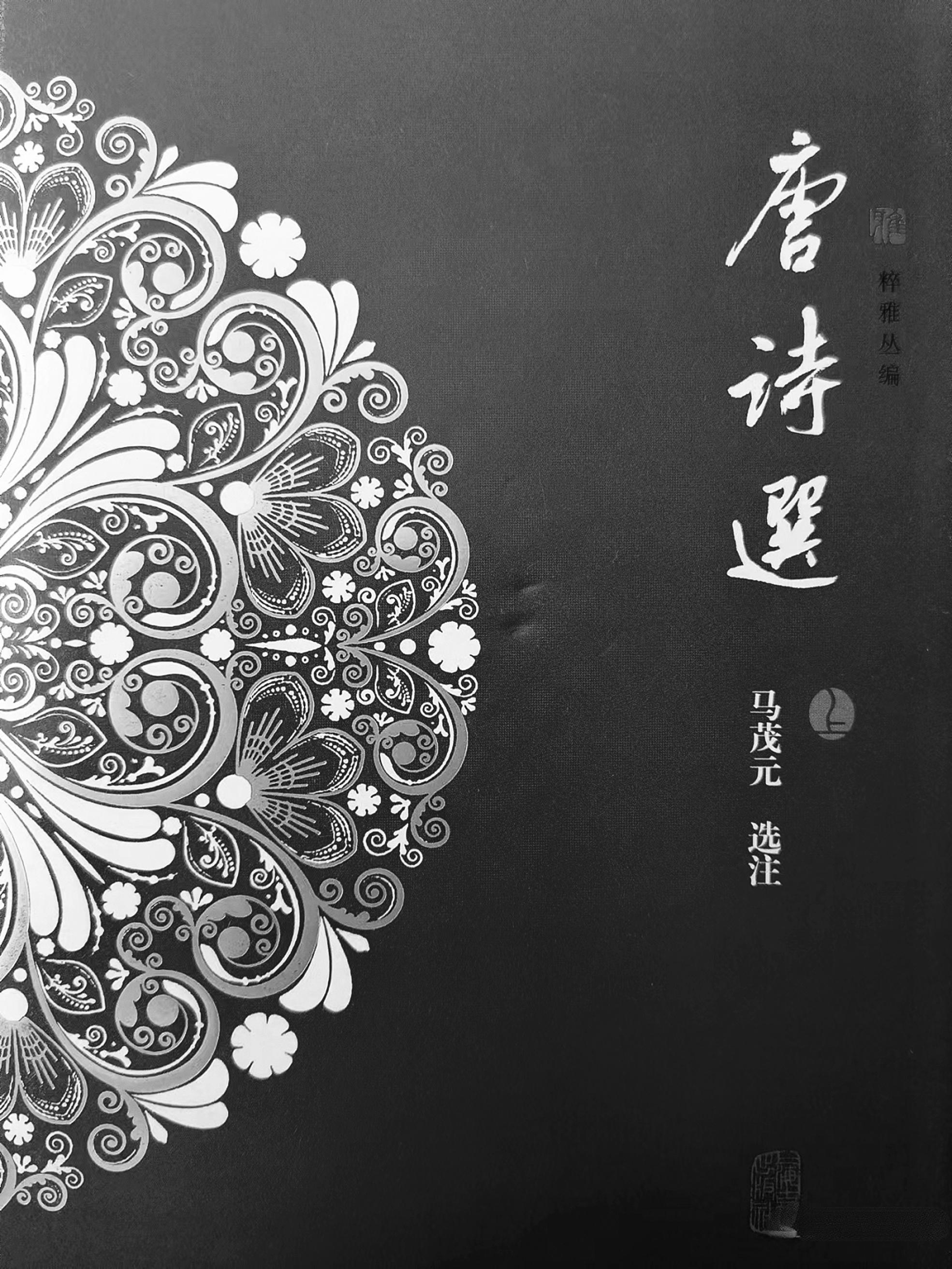□陆远
马茂元先生去世30多年了,学界还经常有人提起他惊人的记忆力:据说他是整个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者中背诵古诗文最多的学者。有人问过他能背多少,老先生自称“五千、五千吧”,而一位资深助手估计,至少在一万首——那一代学人常常谦虚。一万首是什么概念?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奉旨刊刻《全唐诗》,收录唐朝将近300年里2200多位诗人的作品,总数也不超过五万首,马先生一个人能背五分之一!当然这也不奇怪,马先生出生于安徽桐城世家,他的祖父是清代文坛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的殿军马其昶。马茂元从四五岁就跟着祖父学习,以记诵为看家功夫。直到71岁谢世,他浸润古典诗词世界的时间超过一个花甲。
人工智能时代,许多人不免疑惑:AI技术一日千里,今天的我们还有必要背诵古诗吗?我想起前几年火爆的《中国诗词大会》。对于这档曾经引发古典文学热潮的电视节目,不同身份观众的看法却大相径庭。那些面临升学压力的学生家长大概会问:“参加这个比赛有什么用?考试能加分吗?”与此同时,一定还会有不少家长,立刻买一本《唐诗三百首》,督促刚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孩子背起来——不过即便如此,相信这些家长中也总有人会认为,“唐诗宋词?那是小孩子学的吧?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因为需要补上唐诗宋词这一课的,或许恰恰是我们这些成年人。这当然不是为了让人们都回到过去,而是说,今天我们读古诗,是为了更好地做一个现代人。
黄庭坚有一句名言,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所有流行的语言,其实就是时代的投影。在互联网时代读古诗,未必会对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却可以让我们想象和回味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这种“开放性、多元性、包容性”,正是现代精神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诗词大会上那个“满足了对才女所有想象”的武亦姝固然值得点赞,另外两个不起眼的选手更令人称叹:普普通通的淮南民警王纪波和重病缠身的邢台农妇白茹云。诗词与他们现实生活的柴米油盐没有任何“交集”,他们的物质处境也不会因为多背几首唐诗宋词有任何改观,他们对古诗词的爱完全顺从内心,发乎本真。某种程度上说,这样的生活态度与互联网精神是同质的——《长尾理论》的作者、3D Robotics机器人联合创始人安德森说过,互联网的一种重要特征,就是鼓励人们发自内心地追求自己真正喜爱的东西,不管你的爱好多么小众,互联网都可以帮你找到同道,感受到“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快乐。
马茂元先生选注的这本《唐诗选》,初版于20世纪50年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唐诗选本,今天读起来,依然能够感受到编者雅俗共赏的学术品位,就像一滴露珠,照映在太阳光里,也呈现出无限多样的色彩。到了80年代,马先生再度亲手圈阅《全唐诗》,在不放弃自己学术根底与个性的同时,广泛吸取唐诗研究的新成果,在学生赵昌平的协助下,对《唐诗选》进行了修订。今天看来,马先生对数万首唐诗衡文取舍的标准,不是从某种教条的理论出发,而是体味作者鲜活的艺术感受,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立意上求,从气脉上寻,从韵味中辨别”。所谓“观千剑而后识器”,在大量记诵基础上形成的对诗歌艺术价值的感觉能力,是马先生唐诗研究的个性特征,也是他最为雄厚的学术资本。这种感觉能力,往往突破中外古今之限,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按照不少人津津乐道的“迭代理论”,一个社会,越传统的东西折旧率更高,被取代的速度应该更快。但有意思的是,一直到今天,总有一些“传统生活”的文化产物——无论李白、杜甫、陶渊明,还是荷马、乔叟、莎士比亚——还是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及。2016年莎翁和汤显祖逝世400周年时,中英两国几十台传统大戏,几乎场场爆满!为什么李白、杜甫、莎士比亚从不会被“迭代”?因为他们凝聚的是一种文化得以维系的基本价值观和认同感。越是现代的社会,这种认同就越显得弥足珍贵。文化传统这个东西很复杂,它是一套价值,是一些观念,是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套具有公众性的仪式,对文化的感受和传承都需要一套礼仪。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精神,那么,借由唐诗宋词这个窗口重温传统,或许是个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