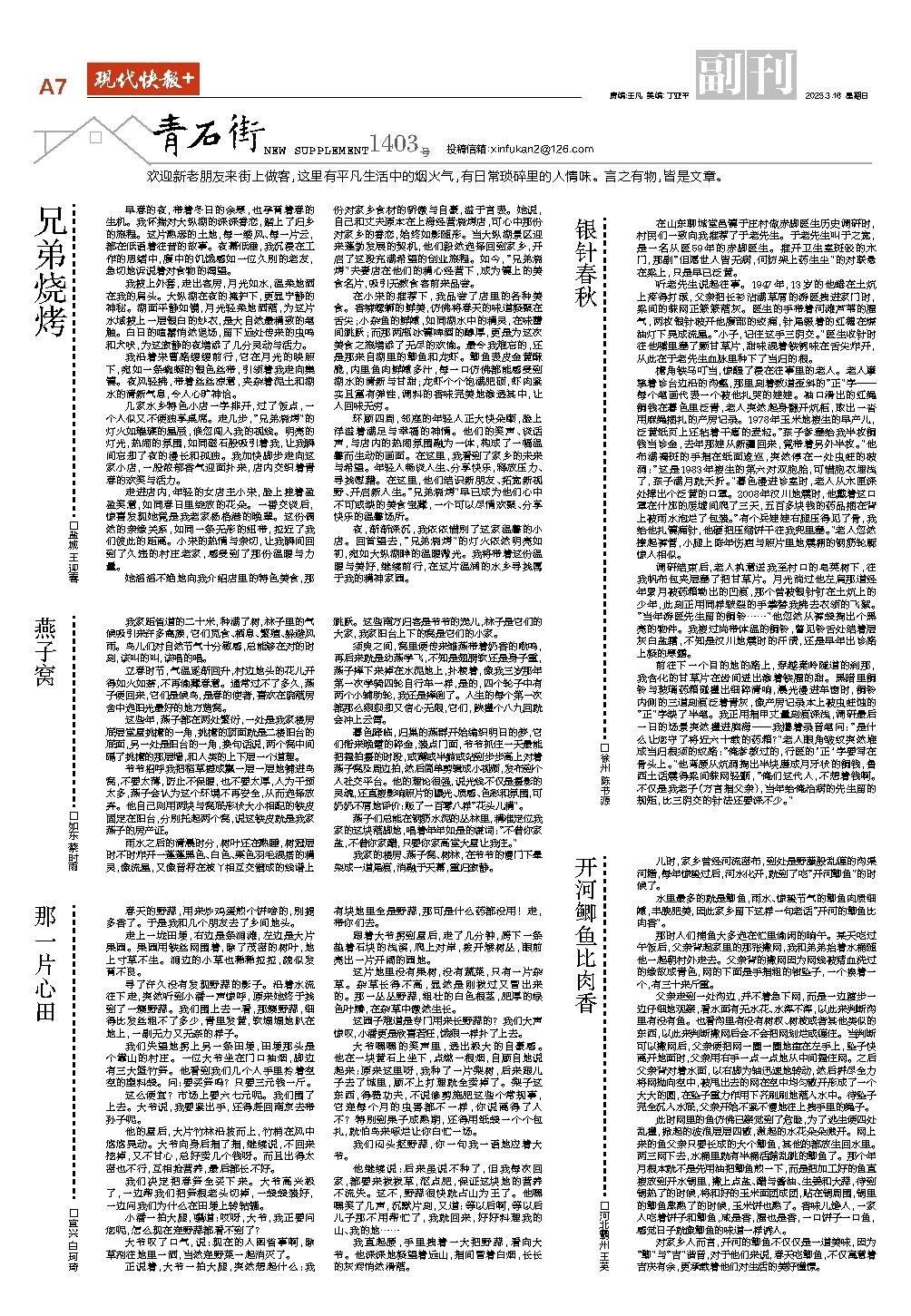□徐州 陈书源
在山东聊城堂邑镇于庄村做赤脚医生历史调研时,村民们一致向我推荐了于老先生。于老先生叫于之宽,是一名从医59年的赤脚医生。推开卫生室斑驳的木门,那副“但愿世人皆无病,何妨架上药生尘”的对联悬在梁上,只是早已泛黄。
听老先生说起往事。1947年,13岁的他蜷在土炕上疼得打滚,父亲把长衫沾满草屑的游医拽进家门时,梁间的蛛网正簌簌落灰。医生的手带着河滩芦苇的腥气,两枚银针破开他腹部的绞痛,针尾缀着的红穗在煤油灯下晃成流星。“小子,记住这手三阴交。”医生收针时往他嘴里塞了颗甘草片,甜味混着铁锈味在舌尖炸开,从此在于老先生血脉里种下了当归的根。
檐角铁马叮当,惊醒了浸在往事里的老人。老人摩挲着诊台边沿的沟壑,那里刻着数道歪斜的“正”字——每个笔画代表一个被他扎哭的娃娃。袖口滑出的红绳铜钱在暮色里泛青,老人突然起身翻开炕柜,取出一沓用麻绳捆扎的产房记录。1978年玉米地接生的早产儿,泛黄纸页上还粘着干瘪的麦粒。“孩子爹塞给我半枚铜钱当诊金,去年那娃从新疆回来,竟带着另外半枚。”他布满褐斑的手指在纸面逡巡,突然停在一处虫蛀的破洞:“这是1983年接生的第六对双胞胎,可惜胞衣埋浅了,孩子满月就夭折。”暮色漫进诊室时,老人从木匣深处捧出个泛黄的口罩。2008年汶川地震时,他戴着这口罩在什邡的废墟间爬了三天,五百多块钱的药品捆在背上被雨水泡烂了包装。“有个兵娃娃右腿压得见了骨,我给他扎镇痛针,他硬把压缩饼干往我兜里塞。”老人忽然撩起裤管,小腿上陈年伤疤与照片里地震棚的钢筋轮廓惊人相似。
调研结束后,老人执意送我至村口的皂荚树下,往我帆布包夹层塞了把甘草片。月光淌过他左肩那道经年累月被药箱勒出的凹痕,那个曾被银针钉在土炕上的少年,此刻正用同样皲裂的手掌替我拂去衣领的飞絮。“当年游医先生留的铜铃……”他忽然从裤袋掏出个黑亮的物件。我接过尚带体温的铜铃,瞥见铃舌处结着层灰白盐霜,不知是汶川地震时的汗渍,还是早年出诊路上凝的寒露。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穿越秦岭隧道的刹那,我含化的甘草片在齿间迸出渗着铁腥的甜。黑暗里铜铃与玻璃药箱碰撞出细碎清响,晨光漫进车窗时,铜铃内侧的三道刻痕泛着青灰,像产房记录本上被虫蛀蚀的“正”字缺了半笔。我正用指甲丈量刻痕深浅,调研最后一日的场景突然撞进脑海——我攥着录音笔问:“是什么让您守了将近六十载的药箱?”老人眼角皱纹突然堆成当归根须的纹路:“俺爹教过的,行医的‘正’字要写在骨头上。”他弯腰从炕洞掏出半块磨成月牙状的铜钱,鲁西土话震得梁间蛛网轻颤,“俺们这代人,不想着钱啊。不仅是我老子(方言指父亲),当年给俺治病的先生留的规矩,比三阴交的针法还要深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