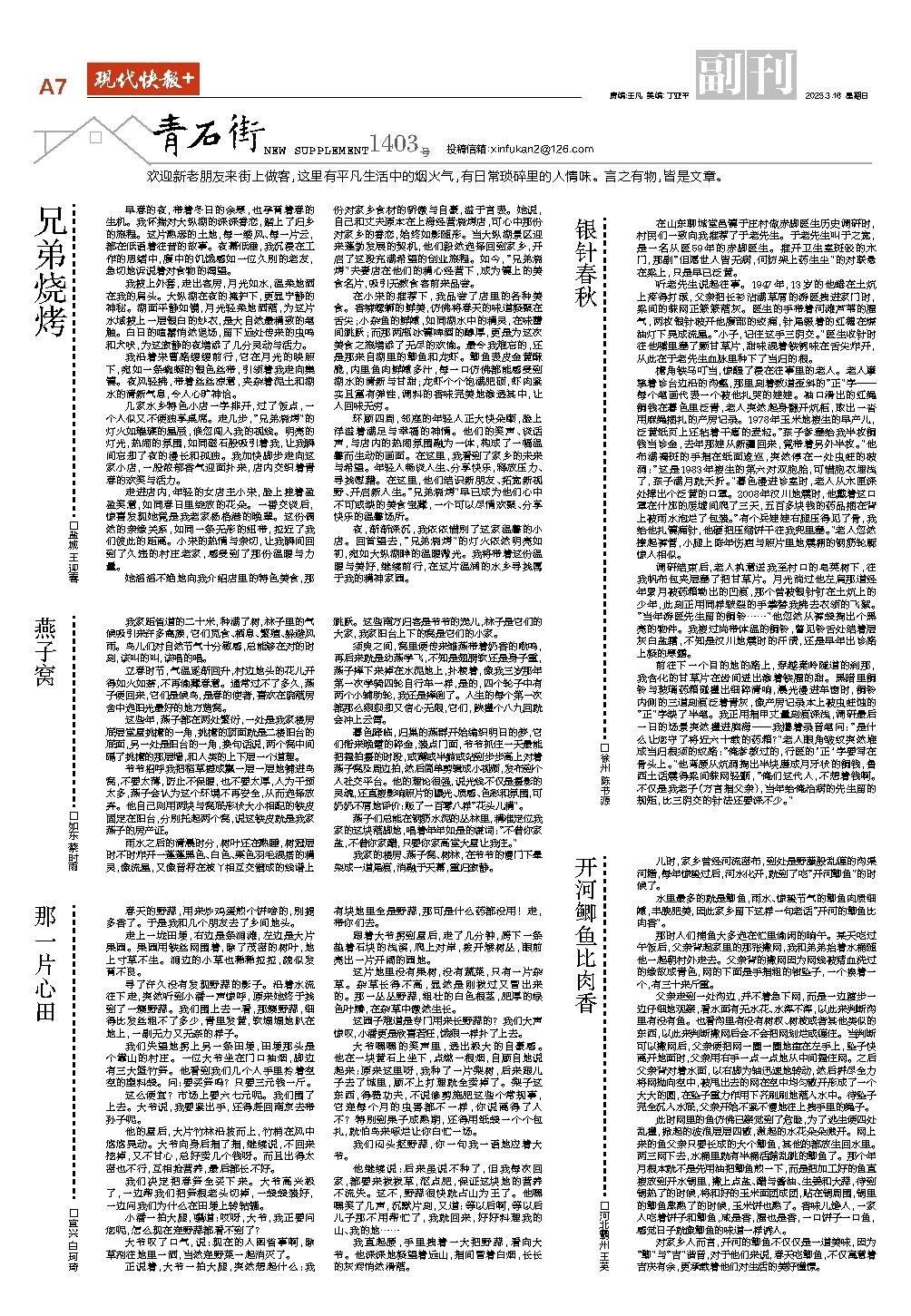□宜兴 白珂琦
春天的野蒜,用来炒鸡蛋煎个饼啥的,别提多香了。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去了乡间地头。
走上一垅田埂,右边是条涧滩,左边是大片果园。果园用铁丝网围着,除了茂密的树叶,地上寸草不生。涧边的小草也稀稀拉拉,貌似发育不良。
寻了许久没有发现野蒜的影子。沿着水流往下走,突然听到小潘一声惊呼,原来她终于找到了一簇野蒜。我们围上去一看,那簇野蒜,细得比发丝粗不了多少,青里发黄,软塌塌地趴在地上,一副无力又无奈的样子。
我们失望地拐上另一条田埂,田埂那头是个靠山的村庄。一位大爷坐在门口抽烟,脚边有三大篮竹笋。他看到我们几个人手里拎着空空的塑料袋。问:要买笋吗?只要三元钱一斤。
这么便宜?市场上要六七元呢。我们围了上去。大爷说,我要紧出手,还得赶回南京去带孙子呢。
他的屋后,大片竹林沿坡而上,竹梢在风中悠悠晃动。大爷向身后指了指,继续说,不回来挖掉,又不甘心,总好卖几个钱呀。而且出得太密也不行,互相抢营养,最后都长不好。
我们决定把春笋全买下来。大爷高兴极了,一边帮我们把笋根老头切掉,一袋袋装好,一边问我们为什么在田埂上转轱辘。
小潘一拍大腿,嚷道:哎呀,大爷,我正要问您呢,怎么现在连野蒜都看不到了?
大爷叹了口气,说:现在的人图省事啊,除草剂往地里一洒,当然连野菜一起消灭了。
正说着,大爷一拍大腿,突然想起什么:我有块地里全是野蒜,那可是什么药都没用!走,带你们去。
跟着大爷拐到屋后,走了几分钟,跨下一条垫着石块的浅溪,爬上对岸,拨开矮树丛,眼前亮出一片开阔的园地。
这片地里没有果树,没有蔬菜,只有一片杂草。杂草长得不高,显然是刚拔过又冒出来的。那一丛丛野蒜,粗壮的白色根茎,肥厚的绿色叶瓣,在杂草中傲然生长。
这园子难道是专门用来长野蒜的?我们大声惊叹,小潘更是欣喜若狂,饿狼一样扑了上去。
大爷嘿嘿的笑声里,透出极大的自豪感。他在一块黄石上坐下,点燃一根烟,自顾自地说起来:原来这里呀,我种了一片梨树,后来跟儿子去了城里,顾不上打理就全卖掉了。梨子这东西,得费功夫,不说修剪施肥这些个常规事,它连每个月的虫害都不一样,你说离得了人不?特别到果子成熟期,还得用纸袋一个个包扎,就怕鸟来啄烂让你白忙一场。
我们闷头抠野蒜,你一句我一语地应着大爷。
他继续说:后来虽说不种了,但我每次回家,都要来拔拔草,沤点肥,保证这块地的营养不流失。这不,野蒜很快就占山为王了。他嘿嘿笑了几声,沉默片刻,又道:等以后啊,等以后儿子那不用帮忙了,我就回来,好好料理我的山、我的地……
我直起腰,手里拽着一大把野蒜,看向大爷。他深深地凝望着远山,指间冒着白烟,长长的灰烬悄然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