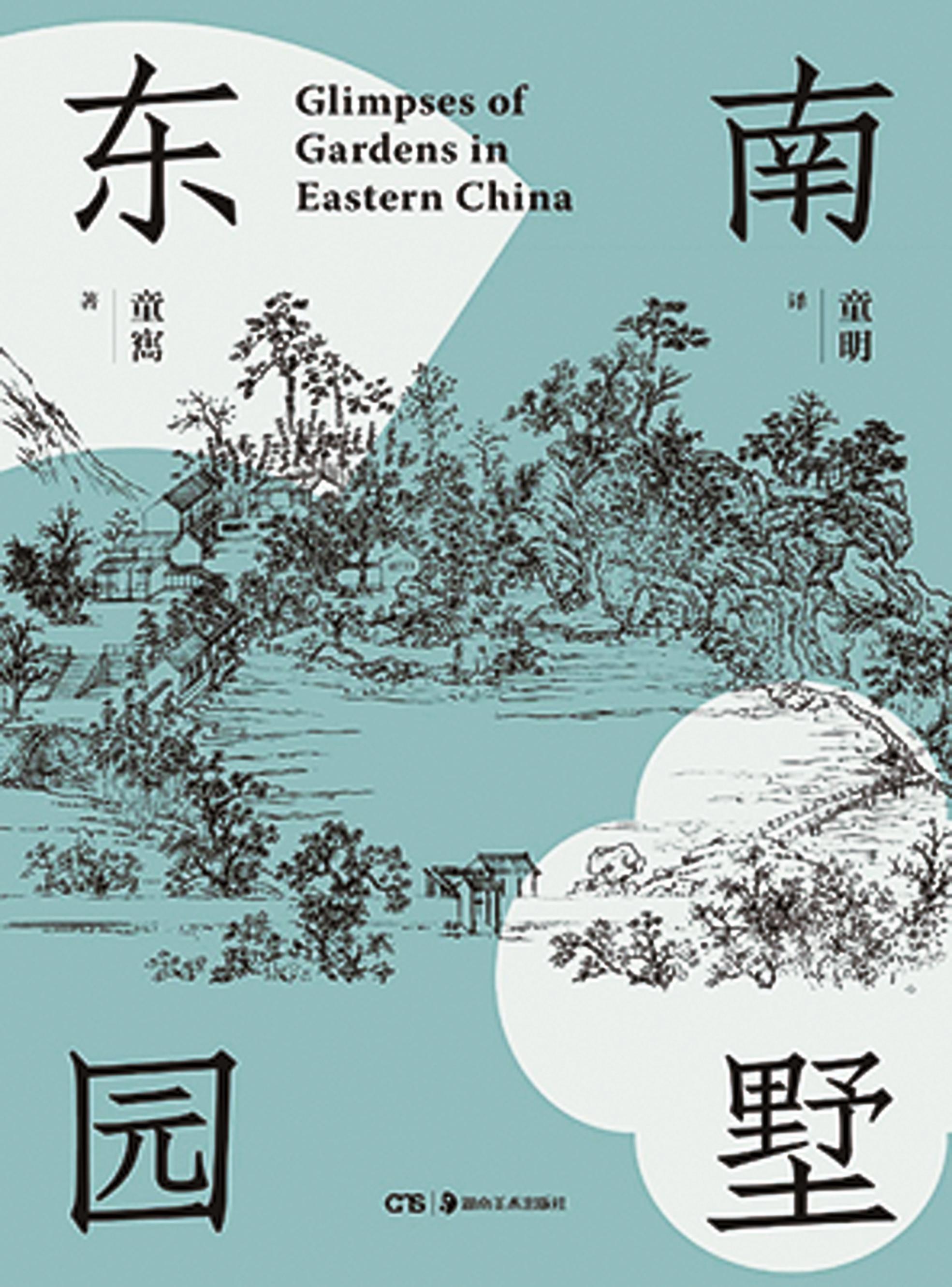□陆远
上世纪70年代末,东南大学教授童寯接待了一个来自欧洲的文化代表团,在交流中他惊讶地发现,许多外国人竟然认为中国古典造园技术是从日本传过来的。作为现代中国最早开始系统研究中国古典园林的学者,这样的误解是童寯无法接受的,年近八旬的老人对家人说:“我要写一篇东西,我们这方面的书太少,日本这方面的书特别多,所以西方人误认为中国园林受到日本的影响,本末倒置。”三年后,童寯写出了《东南园墅》(Glimpses of Gardens in Eastern China)的初稿。第二年,他癌症复发,无论住院治疗还是转诊北京,书稿都随身携带,时加订正。1983年3月,童寯在病榻上最终完成了书稿的修订,两周以后,老人溘然长逝。
对于《东南园墅》,从构思之初童寯就有明确的规划,用英文写作,篇幅不要大,目标读者主要是外国人,最好能和旅游部门挂钩,“可以扩大一点影响”,用今天时髦的话说,这是从古典园林角度“讲好中国故事”的第一次尝试。
虽然这本书的正式出版是童寯身后十几年的事了,但它记录的却是一位以中国园林艺术为心灵寄托的学者超过半世纪的志业。从1932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整整五年间,童寯利用每个星期日,在江浙地区的27个县市勘查研究了109处私家园林,这项工作是在没有任何经费资助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完成的,当时交通不便,童寯基本靠步行完成了踏访。1937年,中国营造学社的刘敦桢、梁思成等同仁在北京读到童寯研究成果《江南园林志》手稿,对其以一己之力构建了中国古典园林研究整个理论框架的建树,大为震撼。那以后的几十年间,童寯先后以英文写成了多篇介绍中国园林艺术的文章。以上这些工作共同构成了《东南园墅》的研究基础。他的学生朱光亚教授回忆:“读童先生的文章,觉得好比啃压缩饼干,一小段文字却有极大的信息浓度,好久才能消化。后来才知道这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披沙拣金功夫的结果。”
1997年,建筑师王澍(他后来成为第一位获得建筑领域国际最高奖普利兹克奖的中国人)读到《东南园墅》的中文译本,正文的第一段话就让他“浑身一激灵,脑袋轰的一下”——童寯写道:“每展中国山水画卷,凡人鲜有纠葛,如此微小斗室茅舍,何以能入硕高之人?一道曲折蜿蜒之弱径,若干横跨湍流之薄板,竟将驴背沉醉之隐者,安稳驮载彼岸?唯览山水画卷而欲得观赏之妙,须先辨识赏画之反常规则。如此不合情理之格制,同样适用中国古典之园林。”王澍说,这个问题一语道破园林语言的特殊逻辑,让人把握中国造园艺术中那种大与小并存,看似矛盾实则和谐的尺度关系,明白了这一点,深浅、进退、开阖、高下、疏密……这些和园林审美有关的术语才有了活的意义。
要欣赏中国园林,多少要了解孕育它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土壤,进而了解园林艺术中包含的中国哲学和美学内涵,懂得它特有的风格和意境。情景交融,物我为一,没有“情”的会心,大概也很难领略“景”的妙趣。寓情于景,触景生情,中国造园艺术就是这一过程的凝聚物。然而如何能以尽可能精炼晓畅的语言,在尽可能小的篇幅内向外国读者传达中国古典园林的文化精髓,并非易事。
在《东南园墅》中,童寯先生以园林与中国画的比拟关系入手,带领读者打开古典园林的柴扉。进而从园林与文人、建筑与布局、装修与家具、叠石艺术、植物配置几个方面,将中国古典园林的构造技法和美学意境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陈述,最终归结为中西文明的特征比较。童寯并不试图陷入中西园林孰优孰劣那种无谓的争论,在他看来,只要能与各自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艺术、哲学和日常生活和谐一致,那么“两者同样伟大”。不过,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童寯当然有坚定的审美立场,他说,“西方园林实则悦目,中国园林意在会心,其一信奉量测标杆,另一追求心智沟通”,而“追根溯源,实为精神与物质之问题”。童寯强调,中国园林文化的本质,是一种“不能度量的艺术”,为了避免僵硬几何、刻板秩序,中国文人甚至愿意不惜代价,以处心积虑、刻意斟酌的不规则性,追求“无规则美”,“幻境迭生,迷津不断”,这是中国古典园林意境最迷人的魅力所在。这背后寄托的,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诗性浪漫的使命”,也就是打破现实秩序的规范,在有限的时空环境中追求无限的精神超越。
本书的末章,在简要回顾了中国园林近3000年的发展史后,童寯列举了江苏、上海、浙江现存的几十座园林,一一点评,既有褒扬,对不足之处亦不惜批评,往往寥寥数语即切中肯綮。在多座古典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东方美学影响日增的当下,不失为绝佳的“江南园林游赏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