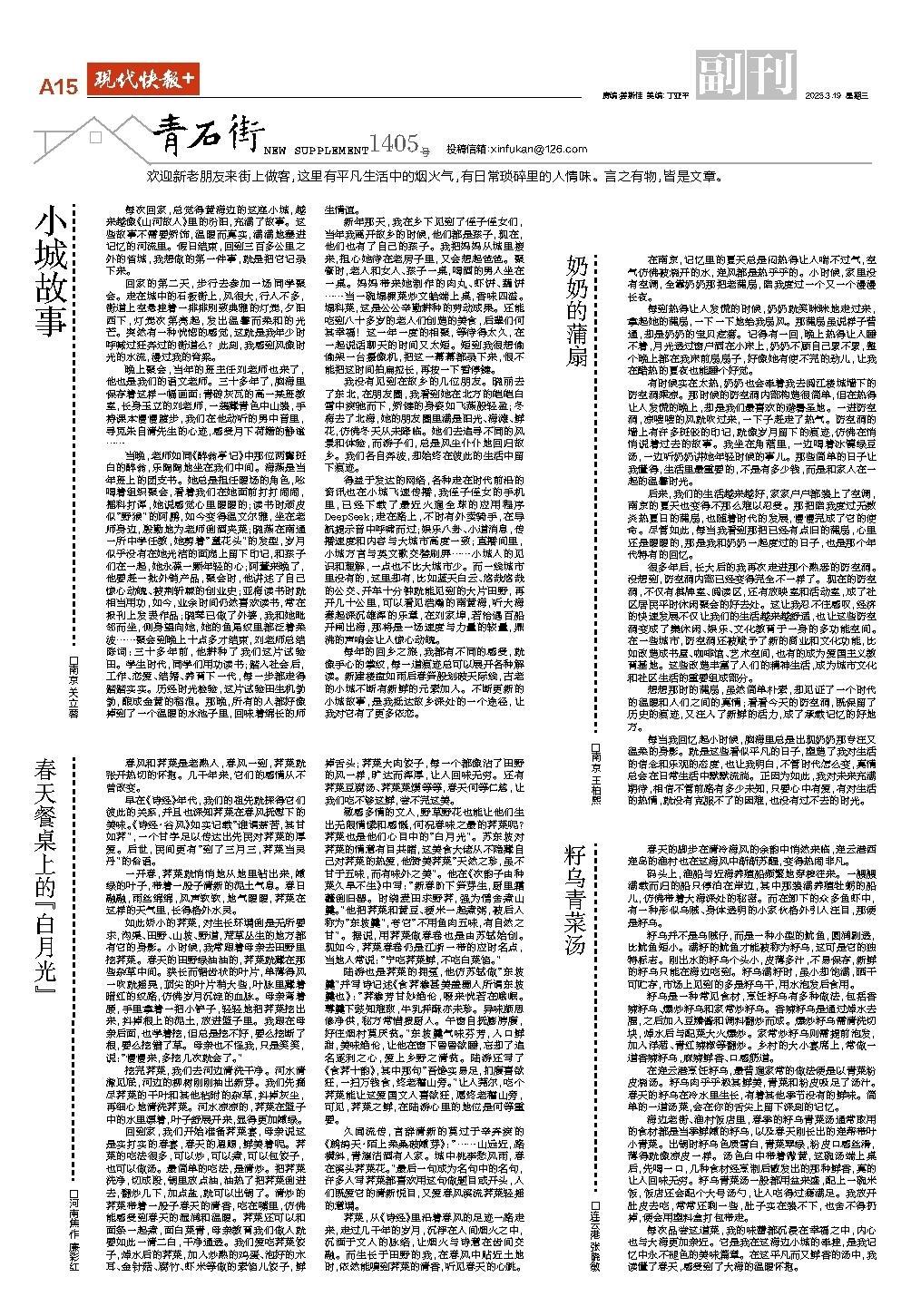□南京 关立蓉
每次回家,总觉得黄海边的这座小城,越来越像《山河故人》里的汾阳,充满了故事。这些故事不需要矫饰,温暖而真实,满满地塞进记忆的河流里。假日结束,回到三百多公里之外的省城,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记录下来。
回家的第二天,步行去参加一场同学聚会。走在城中的石板街上,风很大,行人不多,街道上空悬挂着一排排别致典雅的灯笼,夕阳西下,灯笼次第亮起,发出温馨而柔和的光芒。突然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这就是我年少时呼喊过狂奔过的街道么?此刻,我感到风像时光的水流,漫过我的脊梁。
晚上聚会,当年的班主任刘老师也来了,他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三十多年了,脑海里保存着这样一幅画面:青砖灰瓦的高一某班教室,长身玉立的刘老师,一袭藏青色中山装,手持课本慢慢踱步,我们在他动听的男中音里,寻觅朱自清先生的心迹,感受月下荷塘的静谧……
当晚,老师如同《醉翁亭记》中那位两鬓斑白的醉翁,乐陶陶地坐在我们中间。海燕是当年班上的团支书。她总是担任暖场的角色,吆喝着组织聚会,看着我们在她面前打打闹闹,插科打诨,她说感觉心里暖暖的;读书时顽皮似“野猴”的阿鹏,如今变得温文尔雅,坐在老师身边,殷勤地为老师倒酒夹菜;晓燕在南通一所中学任教,她剪着“童花头”的发型,岁月似乎没有在她光洁的面庞上留下印记,和孩子们在一起,她永葆一颗年轻的心;阿董来晚了,他要赶一批外销产品,聚会时,他讲述了自己惊心动魄、披荆斩棘的创业史;亚梅读书时就相当用功,如今,业余时间仍然喜欢读书,常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晓琴已做了外婆,我和她毗邻而坐,侧身望向她,她的鱼尾纹里都泛着柔波……聚会到晚上十点多才结束,刘老师总结陈词:三十多年前,他耕种了我们这片试验田。学生时代,同学们用功读书;踏入社会后,工作、恋爱、结婚、养育下一代,每一步都走得踏踏实实。历经时光检验,这片试验田生机勃勃,酿成金黄的稻浪。那晚,所有的人都好像掉到了一个温暖的水池子里,回味着绵长的师生情谊。
新年那天,我在乡下见到了侄子侄女们,当年我离开故乡的时候,他们都是孩子,现在,他们也有了自己的孩子。我把妈妈从城里接来,担心她待在老房子里,又会想起爸爸。聚餐时,老人和女人、孩子一桌,喝酒的男人坐在一桌。妈妈带来她制作的肉丸、虾饼、藕饼……当一碗塌棵菜炒文蛤端上桌,香味四溢。塌科菜,这是公公辛勤耕种的劳动成果。还能吃到八十多岁的老人们创造的美食,后辈们何其幸福!这一年一度的相聚,等待得太久,在一起说话聊天的时间又太短。短到我很想偷偷架一台摄像机,把这一幕幕都录下来,恨不能把这时间拍扁拉长,再按一下暂停键。
我没有见到在故乡的几位朋友。晓丽去了东北,在朋友圈,我看到她在北方的皑皑白雪中疾驰而下,矫健的身姿如飞燕般轻盈;冬梅去了北海,她的朋友圈里满是阳光、海滩、鲜花,仿佛冬天从未降临。她们去追寻不同的风景和体验,而游子们,总是风尘仆仆地回归故乡。我们各自奔波,却始终在彼此的生活中留下痕迹。
得益于发达的网络,各种走在时代前沿的资讯也在小城飞速传播,我侄子侄女的手机里,已经下载了最近火遍全球的应用程序DeepSeek;走在路上,不时有外卖骑手,在导航提示音中呼啸而过;娱乐八卦、小道消息,传播速度和内容与大城市高度一致;直播间里,小城方言与英文歌交替刷屏……小城人的见识和理解,一点也不比大城市少。而一线城市里没有的,这里却有,比如蓝天白云、悠哉悠哉的公交、开车十分钟就能见到的大片田野,再开几十公里,可以看见浩瀚的南黄海,听大海奏起深沉雄浑的乐章,在刘家埠,若恰遇百船开闸出海,那将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较量,鼎沸的声响会让人惊心动魄。
每年的回乡之旅,我都有不同的感受,就像手心的掌纹,每一道痕迹总可以展开各种解读。新建楼盘如雨后春笋般划破天际线,古老的小城不断有新鲜的元素加入。不断更新的小城故事,是我抵达故乡深处的一个途径,让我对它有了更多依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