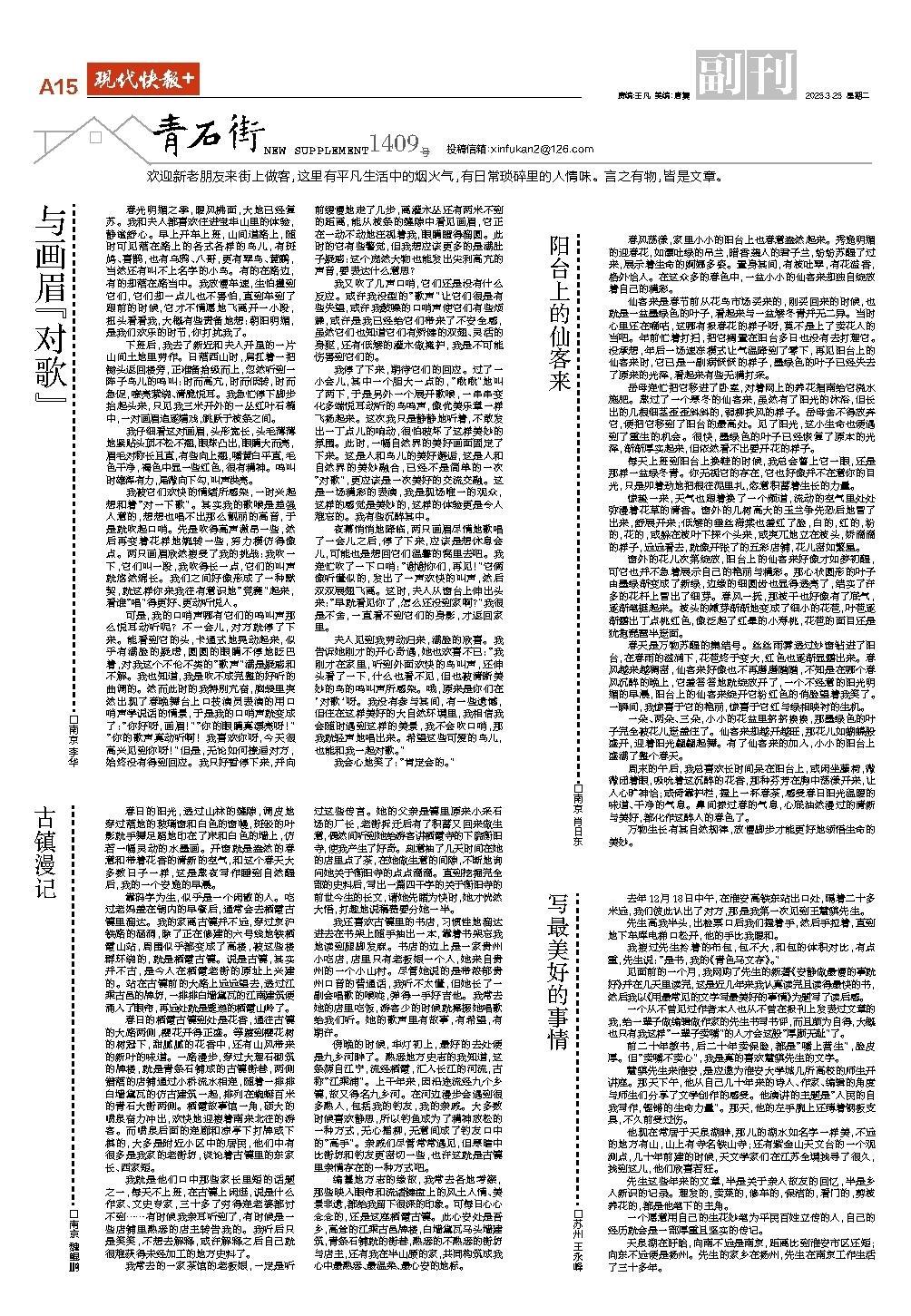□南京 魏鲲鹏
春日的阳光,透过山林的缝隙,调皮地穿过落地的玻璃窗和白色的窗幔,斑驳的叶影就手舞足蹈地印在了床和白色的墙上,仿若一幅灵动的水墨画。开窗就是盎然的春意和带着花香的清新的空气,和这个春天大多数日子一样,这是熬夜写作睡到自然醒后,我的一个安逸的早晨。
靠码字为生,似乎是一个闲散的人。吃过老妈盖在锅内的早餐后,通常会去栖霞古镇里溜达。我的家离古镇并不远,穿过京沪铁路的涵洞,除了正在修建的六号线地铁栖霞山站,周围似乎都变成了高楼,被这些楼群环绕的,就是栖霞古镇。说是古镇,其实并不古,是今人在栖霞老街的原址上兴建的。站在古镇前的大路上远远望去,透过江乘古邑的牌坊,一排排白墙黛瓦的江南建筑便涌入了眼帘,再远处就是逶迤的栖霞山岭了。
春日的栖霞古镇到处是花香,通往古镇的大路两侧,樱花开得正盛。等踱到樱花树的树冠下,甜腻腻的花香中,还有山风带来的新叶的味道。一路漫步,穿过大理石砌筑的牌楼,就是青条石铺成的古镇街巷,两侧错落的店铺通过小桥流水相连,随着一排排白墙黛瓦的仿古建筑一起,排列在蜿蜒百米的青石大街两侧。栖霞故事馆一角,硕大的喷泉奋力冲出,欢快地迎接着南来北往的游客。而喷泉后面的连廊和凉亭下打牌或下棋的,大多是附近小区中的居民,他们中有很多是我家的老街坊,谈论着古镇里的东家长、西家短。
我就是他们口中那些家长里短的话题之一,每天不上班,在古镇上闲逛,说是什么作家、文史专家,三十多了穷得连老婆都讨不到……有时候我亲耳听到了,有时候是一些店铺里熟悉的店主转告我的。我听后只是笑笑,不想去解释,或许解释之后自己就很难获得未经加工的地方史料了。
我常去的一家茶馆的老板娘,一定是听过这些传言。她的父亲是镇里原来小采石场的厂长,老街拆迁后有了积蓄又回来做生意,偶然间听到她给游客讲栖霞寺的下院衡阳寺,使我产生了好奇。刻意抽了几天时间在她的店里点了茶,在她做生意的间隙,不断地询问她关于衡阳寺的点点滴滴。直到挖掘完全部的史料后,写出一篇四千字的关于衡阳寺的前世今生的长文,请她先睹为快时,她才恍然大悟,打趣地说稿费要分她一半。
我还喜欢古镇里的书店,习惯性地溜达进去在书架上随手抽出一本,靠着书架忘我地读到腿脚发麻。书店的边上是一家贵州小吃店,店里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她来自贵州的一个小山村。尽管她说的是带浓郁贵州口音的普通话,我听不太懂,但她长了一副会唱歌的喉咙,弹得一手好吉他。我常去她的店里吃饭,游客少的时候就撺掇她唱歌给我们听。她的歌声里有故事,有希望,有期许。
傍晚的时候,华灯初上,最好的去处便是九乡河畔了。熟悉地方史志的我知道,这条源自江宁,流经栖霞,汇入长江的河流,古称“江乘浦”。上千年来,因沿途流经九个乡镇,故又得名九乡河。在河边漫步会遇到很多熟人,包括我的钓友,我的亲戚。大多数时候喜欢静思,所以钓鱼成为了精神放松的一种方式,无心插柳,无意间成了钓友口中的“高手”。亲戚们尽管常常遇见,但寒暄中比街坊和钓友更密切一些,也许这就是古镇里亲情存在的一种方式吧。
编纂地方志的缘故,我常去各地考察,那些映入眼帘和流诸键盘上的风土人情、美景非遗,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可每日心心念念的,还是这座栖霞古镇。此心安处是吾乡,高耸的江乘古邑牌楼,白墙黛瓦马头墙建筑,青条石铺就的街巷,熟悉的不熟悉的街坊与店主,还有我在半山腰的家,共同构筑成我心中最熟悉、最温柔、最心安的地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