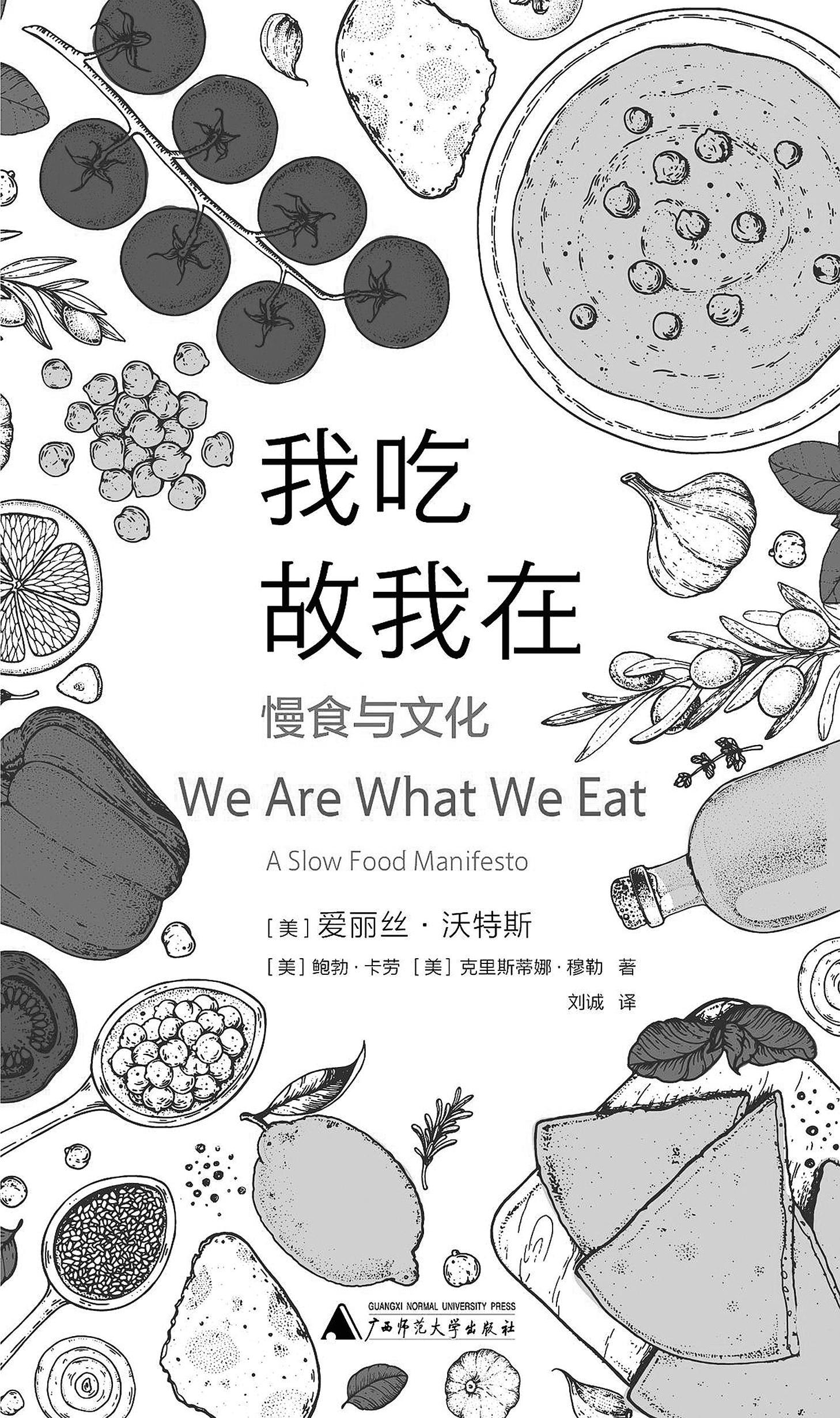□陆远
几周前参加一个读书分享会,嘉宾刘擎教授感慨许多人往往不大能分得清“饿”和“馋”的区别:饿是一种生理本能,馋却是一种精神状态。对于地球上大多数人来说,21世纪是一个物质丰裕的年代,但在饮食方面,人类依然面临着许多严峻问题。这不仅仅指的是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人类依然受到贫困和饥饿的威胁,更包括那些衣食无忧的人们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精神困境。换句话说,摆脱了“饿”之困扰的人们发现,“馋”带来的麻烦同样棘手。
18世纪法国传奇人物,《厨房里的哲学家》作者布里亚-萨瓦兰说过:“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人民吃什么样的东西。”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不少欧美发达国家的青年人(比如史蒂夫·乔布斯)就开始从饮食的角度出发,反思和批判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现代性问题。当时的美国餐饮市场,几乎被连锁快餐店、超级市场、工业化生产的冷冻食品和速食罐头所占领,所谓“烹饪”,不过是将食物从冰箱拿到微波炉加热而已。那些看上去丰富多样,琳琅满目的各色美食,不过都是口味千篇一律的预制品,在资本和工业化的笼罩下,烹饪和饮食都失去了鲜活的意义,更不用说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对健康的潜在威胁。出于对餐饮业背后的资本主义、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反抗,不少人身体力行,倡导一种健康、自然的饮食方式,1971年8月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开业的“潘尼斯之家”餐厅就是这一风潮重要的引领者之一。直到今天,它始终强调使用本地农场生产的新鲜有机食材,坚持用简单、传统的烹饪方式,凸显食材的本来风味,也由此开创了后来被称为“从农场到餐桌”的运动,进而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文化现象。2021年潘尼斯之家迎来50岁生日之际,它的创始人,美国传奇烹饪师、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爱丽丝·沃特斯将其毕生坚守的饮食主张和实践经验总结成了《我吃故我在》一书。
沃特斯将自己的主张总结为“慢食文化”,而把那种与之相对的,在20世纪日益成为美国主流的饮食习惯称为“快餐文化”。《我吃故我在》就是沃特斯批判“快餐文化”,倡导“慢食文化”的一份宣言,用她自己的话说,是一份“关于饮食对个人生活和世界影响的宣言”,也是“关于人类如何通过行动改变历史进程的宣言”。
从自己在厨房和餐厅的日常经验出发,思考的落脚点却直面人类社会的总体困境,这是《我吃故我在》的深刻之处和价值所在。沃特斯从“方便”“统一”“唾手可得”“广告”“越多越好”和“速度”等几个方面总结“快餐文化”的弊端。她并不否认生产力进步和技术改良对改善人类生活产生的巨大正面意义,但更提醒人们警惕这背后潜移默化的风险和侵蚀。比如,当人们狂热地崇拜“方便”时,却忘记了“艰难”本身就是人类经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那些被从厨房里和饭桌上硬挤出来的时间依然被碎片化为各种无厘头的消遣;比如,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随时随地吃到任何想吃到的东西,却忘记了无论荤素所有的食材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它们自己生长成熟的生命周期,“唾手可得”的欲望背后,是时空紊乱的现代症候;比如,今天的食品超市和自助餐厅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丰饶肥美的画面,仿佛时时刻刻在召唤,“来吃吧,越多越好!”其结果,就是触目惊心的肥胖、浪费和污染;再比如,“速度是快餐文化的发动机,是所有快餐价值观的推动力”,它意味着一切事物都应该越快越好,只要没有立刻得到满足,人们就会产生挫败感乃至陷入深深焦虑。
与“快餐文化”相反,“慢食文化”重拾那些在工业社会渐渐被人们遗忘的价值:生物多样性、四季时令、照料、工作的乐趣、简单、万物生息等等,主张尽可能将人类的起居重新置于自然循环和节奏中去,进而采取行动,从饮食入手,维护身心健康,比如自己做饭,少吃外卖,拒绝预制菜,采买新鲜食材;比如和家人一起吃饭,吃时令果蔬,勤俭持家,有机低碳等。沃特斯试着提醒水泥丛林中终日奔忙的现代人,停一停,慢下来,耐心点,用饮食去关爱、照料、聆听自己身体和感官。这么做并不是主张人们回到某种理想的过去,也不是要人们退守历史上从未真正存在过的前工业文明的乌托邦世界,而是通过食物将普遍的人类价值带入不断发展的未来。
坦率地说,在“加速”日益成为生活节奏主旋律的现代社会,沃特斯倡导的慢食文化恐怕很难成为主流。但近半个世纪以来她知行合一的实践依然在时刻鼓舞和提醒我们,慢食价值是人类共同分享的自然遗产,它们就在那里,等待着每个人的觉醒。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尝一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