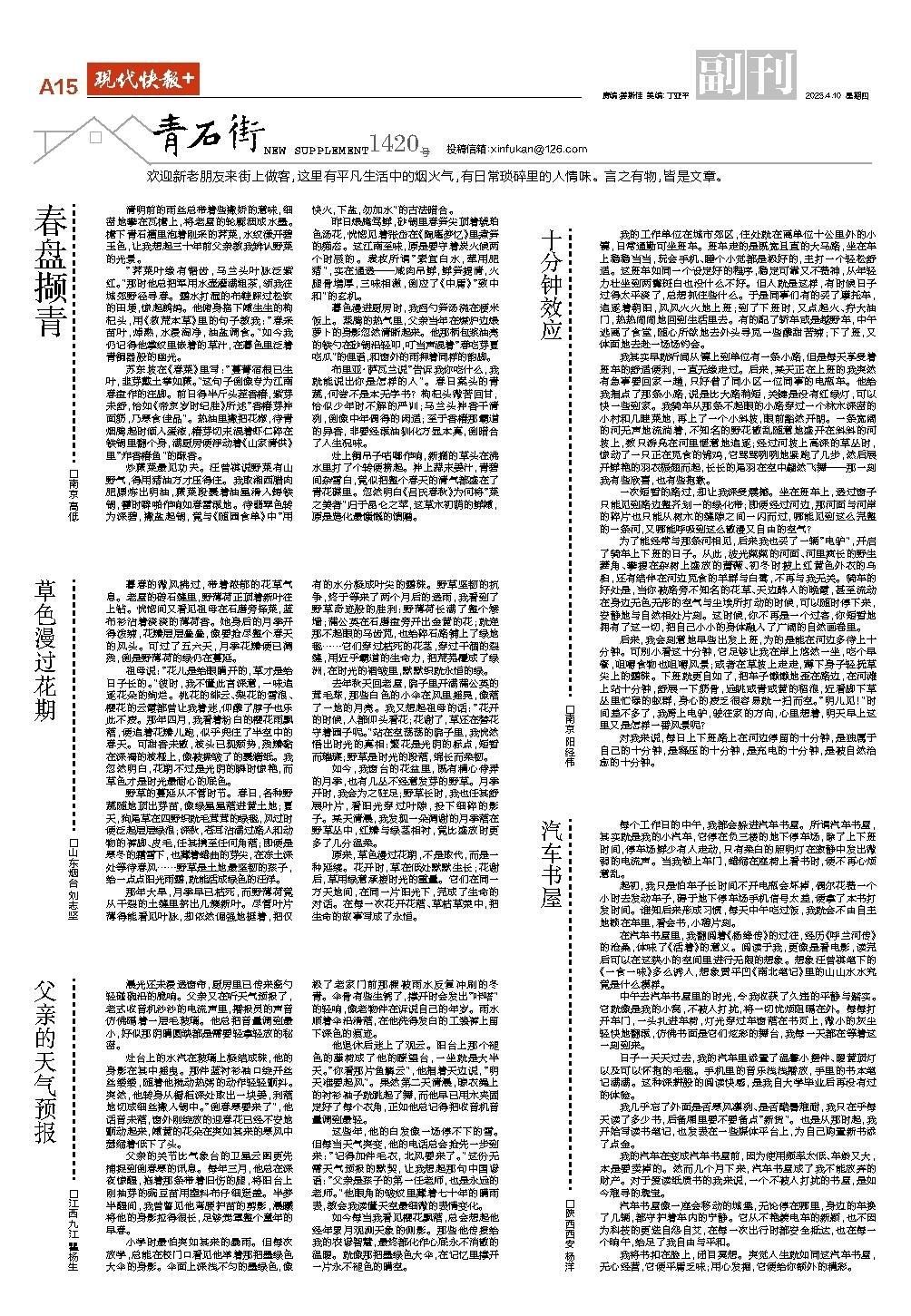□山东烟台 刘志坚
暮春的微风拂过,带着浓郁的花草气息。老屋的砖石缝里,野薄荷正顶着新叶往上钻。恍惚间又看见祖母在石磨旁择菜,蓝布衫沾着淡淡的薄荷香。她身后的月季开得泼辣,花瓣层层叠叠,像要抢尽整个春天的风头。可过了五六天,月季花瓣便已凋残,倒是野薄荷的绿仍在蔓延。
祖母说:“花儿是给眼睛开的,草才是给日子长的。”彼时,我不懂此言深意,一味追逐花朵的绚烂。桃花的绯云、梨花的雪浪、樱花的云霞都曾让我着迷,仰酸了脖子也乐此不疲。那年四月,我看着粉白的樱花雨飘落,便追着花瓣儿跑,似乎兜住了半空中的春天。可甜香未散,枝头已现颓势,残瓣黏在深褐的枝桠上,像被揉皱了的裹糖纸。我忽然明白,花期不过是光阴的瞬时惊艳,而草色才是时光最耐心的底色。
野草的蔓延从不管时节。春日,各种野蔬随地顶出芽苗,像绿星星落进黄土地;夏天,狗尾草在四野织就毛茸茸的绿毯,风过时便泛起层层绿浪;深秋,苍耳沾满过路人和动物的裤脚、皮毛,任其携至任何角落;即便是寒冬的霜雪下,也藏着蜷曲的芽尖,在冻土深处等待春风……野草是土地最坚韧的孩子,给一点点阳光雨露,就能活成绿色的汪洋。
那年大旱,月季早已枯死,而野薄荷竟从干裂的土缝里挤出几簇新叶。尽管叶片薄得能看见叶脉,却依然倔强地挺着,把仅有的水分凝成叶尖的露珠。野草坚韧的抗争,终于等来了两个月后的透雨,我看到了野草奇迹般的胜利:野薄荷长满了整个矮墙;蒲公英在石磨盘旁开出金黄的花;就连那不起眼的马齿苋,也给碎石路铺上了绿地毯……它们穿过枯死的花茎,穿过干涸的裂缝,用近乎霸道的生命力,把荒芜覆成了绿洲,在时光的褶皱里,默默织就永恒的绿。
去年秋天回老屋,院子里开满蒲公英的茸毛球,那些白色的小伞在风里摇晃,像落了一地的月亮。我又想起祖母的话:“花开的时候,人都仰头看花;花谢了,草还在替花守着园子呢。”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我恍然悟出时光的真相:繁花是光阴的标点,短暂而璀璨;野草是时光的段落,绵长而柔韧。
如今,我窗台的花盆里,既有精心侍弄的月季,也有几丛不经意发芽的野草。月季开时,我会为之驻足;野草长时,我也任其舒展叶片,看阳光穿过叶隙,投下细碎的影子。某天清晨,我发现一朵凋谢的月季落在野草丛中,红瓣与绿茎相衬,竟比盛放时更多了几分温柔。
原来,草色漫过花期,不是取代,而是一种延续。花开时,草在低处默默生长;花谢后,草用绿意承接时光的重量。它们在同一方天地间,在同一片阳光下,完成了生命的对话。在每一次花开花落、草枯草荣中,把生命的故事写成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