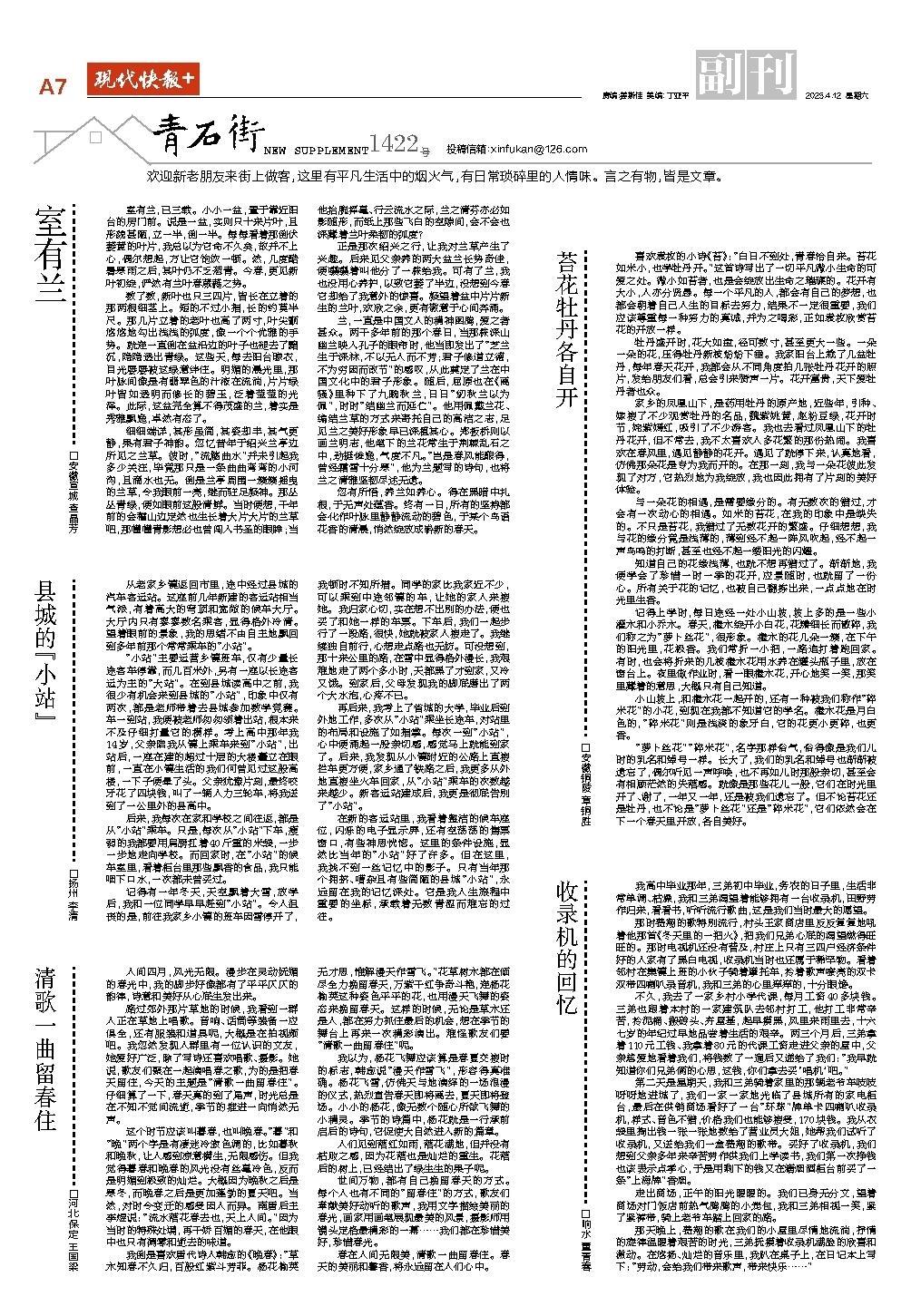□安徽宣城 查晶芳
室有兰,已三载。小小一盆,置于靠近阳台的房门前。说是一盆,实则只十来片叶,且形貌甚陋,立一半,倒一半。每每看着那倒伏萎黄的叶片,我总以为它命不久矣,故并不上心,偶尔想起,方让它饱饮一顿。然,几度酷暑寒雨之后,其叶仍不乏葱青。今春,更见新叶初绽,俨然有兰叶春葳蕤之势。
数了数,新叶也只三四片,皆长在立着的那两根细茎上。短的不过小指,长的约莫半尺。那几片立着的老叶也高了两寸,叶尖颤悠悠地勾出浅浅的弧度,像一个个优雅的手势。就连一直倒在盆沿边的叶子也褪去了黯沉,隐隐透出青绿。这些天,每去阳台晾衣,目光屡屡被这绿意绊住。明媚的晨光里,那叶脉间像是有翡翠色的汁液在流淌,片片绿叶皆如透明而修长的碧玉,泛着莹莹的光泽。此际,这盆完全算不得茂盛的兰,着实是秀雅飘逸,卓然有态了。
细细端详,其形虽简,其姿却丰,其气更静,果有君子神韵。忽忆昔年于绍兴兰亭边所见之兰草。彼时,“流觞曲水”并未引起我多少关注,毕竟那只是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沟,且滴水也无。倒是兰亭周围一簇簇摇曳的兰草,令我眼前一亮,继而驻足凝神。那丛丛青绿,便如眼前这般清鲜。当时便想,千年前的会稽山边定然也生长着大片大片的兰草吧,那幢幢青影想必也曾闯入书圣的眼眸;当他抬腕挥毫、行云流水之际,兰之清芬亦必如影随形,而纸上那些飞白的空隙间,会不会也深藏着兰叶柔韧的弧度?
正是那次绍兴之行,让我对兰草产生了兴趣。后来见父亲养的两大盆兰长势奇佳,便嚷嚷着叫他分了一株给我。可有了兰,我也没用心养护,以致它萎了半边,没想到今春它却给了我意外的惊喜。凝望着盆中片片新生的兰叶,欢欣之余,更有敬意于心间奔涌。
兰,一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图腾,爱之者甚众。两千多年前的那个春日,当那株深山幽兰映入孔子的眼帘时,他当即发出了“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的感叹,从此奠定了兰在中国文化中的君子形象。随后,屈原也在《离骚》里种下了九畹秋兰,日日“纫秋兰以为佩”,时时“结幽兰而延伫”。他用佩戴兰花、编结兰草的方式来寄托自己的高洁之志,足见兰之美好形象早已深植其心。郑板桥则以画兰明志,他笔下的兰花常生于荆棘乱石之中,劲挺俊逸,气度不凡。“岂是春风能酿得,曾经霜雪十分寒”,他为兰题写的诗句,也将兰之清雅坚韧尽述无遗。
忽有所悟,养兰如养心。得在黑暗中扎根,于无声处蕴香。终有一日,所有的坚持都会化作叶脉里静静流动的碧色,于某个鸟语花香的清晨,悄然绽放成崭新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