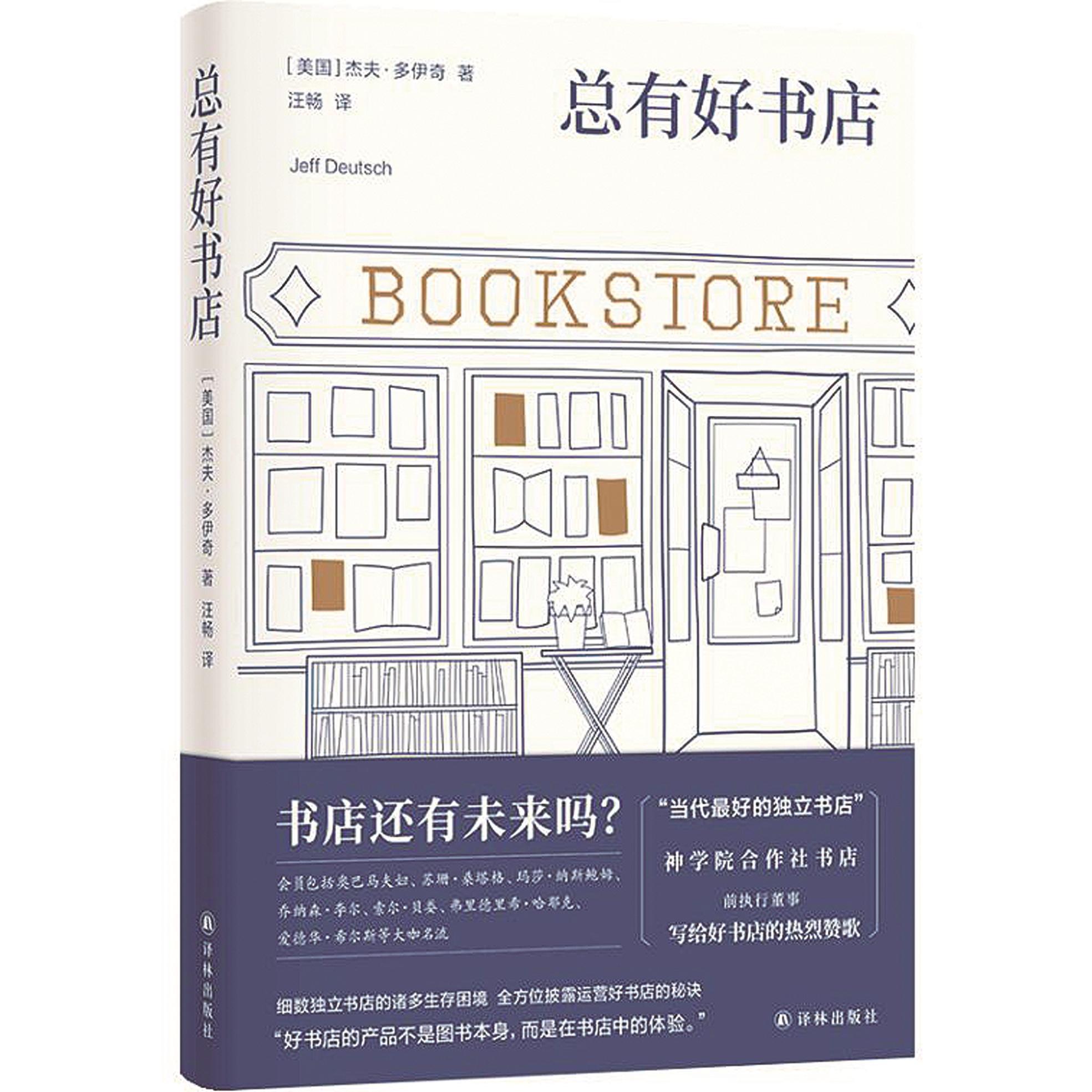□张露
1961年,美国芝加哥的5名大学生在地下室成立了一家书店。其初衷是为芝加哥大学、芝加哥神学院及附近的学生、教职工提供专业书籍。
如今,这家曾经位于地下室的书店聚集了各种年龄和不同背景的热情读者,它是让苏珊·桑塔格、玛莎·纳斯鲍姆、斯拉沃热·齐泽克、扎迪·史密斯、爱德华·希尔斯等人都为之着迷的书店。它就是芝加哥神学院合作社书店。
《总有好书店》的作者杰夫·多伊奇是继杰克·塞拉后的第二任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经理,被誉为“献身于书店的灵魂”。从2014年到2024年,他为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服务了整整10年。他把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成功归结于颇具格调的选书品位和丰富的藏书,为浏览和思考而打造的沉浸式空间,为读者创造的沉浸于书店的慢时光,以及打造将成员精神联结在一起的社区。
在多伊奇看来,好书店的蓬勃兴旺从不指望畅销作品,而是成千上万的单一“产品”。这些“产品”被耐心地放在书架上,等候着命中注定的读者前来翻阅。这一点构成了好书店的非凡之处,或许更是独特之处。
当亚马逊等电商用亏本售书引流、算法精准投喂书单,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却像一位固执的老派绅士,坚持用“低效”对抗这个时代,坚持“以一种对待文物的方式耐心出售图书”,为每本书找到它的读者。
2019年,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售出的2.8万本书中,有近1.7万本是以单本的形式销售的。也就是说,这1.7万本书中的每一本都为一位独特的读者所寻求。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和他们的读者欣然拥抱了书店的低效之处。这些低效之处绝不是对时间的挥霍,而是创建一家好书店至关重要的因素。
为维持运营,杰夫·多伊奇大胆地选择了另一条道路:摒弃传统的低买高卖的零售模式,转而从礼物经济中获得资金,用图书之外的商品,诸如咖啡、笔记本、贺卡,以支持利润微薄且销售缓慢的图书销售事业。
好书店的标准是什么?多伊奇说:“好书店虽然销售图书,它的主要产品是‘浏览的体验’。”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产品就是空间本身,正是书籍塑造了浏览的空间。
现如今,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早已不再是一个合作社,也不再位于地下室,搬迁到了芝加哥57街。建筑师斯坦利·泰格曼在设计新的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时,复刻了老书店的“迷失”美学。他设计了一系列“象征性空洞”,其多边形组合排列的方式构成了一座迷宫;这些人形空洞的“窗口”,诱惑着顾客走进下一个空间。泰格曼说:“所需要的是,随处可读的书籍。”
斯坦利·泰格曼构建了内部结构,而书商规划了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书籍分类。书商的分类法往往构成了书店身份的一部分,如何整理藏书则决定了浏览的逻辑性和意外性。
通过巧妙的书架陈列和别出心裁的书籍分区,神学院合作社书店打造了书籍的迷宫世界。每一本书最初都是凭借其在书海中的位置被发现,接着与其他书籍分离,最后被单独阅读;所有书籍只有通过与其他书籍的关联,才能真正被读者发现。由此,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创造了一个互相联结的书籍世界。
无怪乎《美国大城市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说:“神学院合作社书店充满了改变生活的惊喜和未知的宝藏;每当你转过一个角落,你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新发现。”
据杰克·塞拉回忆,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昌德拉塞卡希望把自己的骨灰撒在几个对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神学院合作书店门前的草地。
书店的困境绝非数字时代的独有产物。早在18世纪,狄德罗编纂《百科全书》时便哀叹“图书业每况愈下,图书销售不再盈利”。自那以后,对书店的哀叹从未停息。多伊奇认为,人们对理想图书业的怀旧之情很可能是凭空虚构的,“好书店从没有在商业上有所建树”。
也正因此,这部神学院合作社书店的运营自白,更多的是多伊奇写给好书店的深情赞歌,更是写给所有“纸质书遗民”的告白。在一键购物时代,在纸质书式微时代,书店不仅能够生存下去,而且能够实现其最高愿景——通过好书店的力量,提供条件,让读者放缓步伐,看到更广阔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