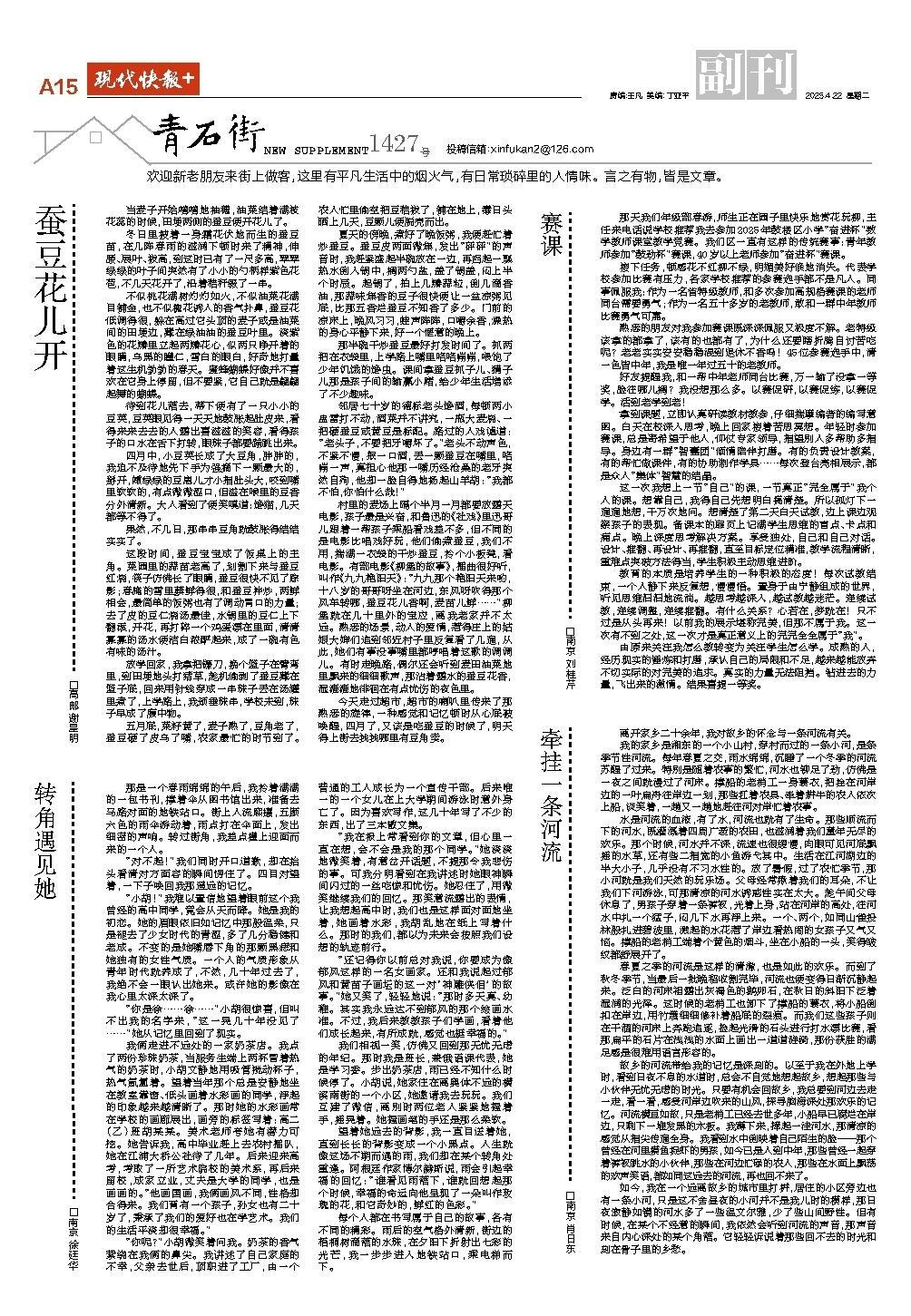□高邮 谢星明
当麦子开始噌噌地抽穗,油菜结着满枝花蕊的时候,田埂两侧的蚕豆便开花儿了。
冬日里披着一身霜花伏地而生的蚕豆苗,在几阵春雨的滋润下顿时来了精神,伸腰、展叶、拔高,到这时已有了一尺多高,翠翠绿绿的叶子间突然有了小小的勺柄样紫色花苞,不几天花开了,沿着秸秆缀了一串。
不似桃花满树灼灼如火,不似油菜花满目铺金,也不似槐花诱人的香气扑鼻,蚕豆花低调得很,躲在高过它头顶的麦子或是油菜间的田埂边,藏在绿油油的蚕豆叶里。淡紫色的花瓣里立起两瓣花心,似两只睁开着的眼睛,乌黑的瞳仁,雪白的眼白,好奇地打量着这生机勃勃的春天。蜜蜂蝴蝶好像并不喜欢在它身上停留,但不要紧,它自己就是翩翩起舞的蝴蝶。
待到花儿落去,蒂下便有了一只小小的豆荚,豆荚眼见得一天天地鼓胀起肚皮来,看得来来去去的人露出喜滋滋的笑容,看得孩子的口水在舌下打转,眼珠子都要蹦跳出来。
四月中,小豆荚长成了大豆角,胖胖的,我迫不及待地先下手为强摘下一颗最大的,掰开,嫩绿绿的豆崽儿才小指肚头大,咬到嘴里软软的,有点微微涩口,但溢在喉里的豆香分外清新。大人看到了便笑嗔道:馋猫,几天都等不得了。
果然,不几日,那串串豆角就鼓胀得结结实实了。
这段时间,蚕豆宝宝成了饭桌上的主角。菜园里的蒜苗老高了,划割下来与蚕豆红烧,筷子仿佛长了眼睛,蚕豆很快不见了踪影;春腌的雪里蕻鲜得很,和蚕豆拌炒,两鲜相会,最简单的饭粥也有了调动胃口的力量;去了皮的豆仁烧汤最佳,水锅里的豆仁上下翻滚,开花,再打碎一个鸡蛋漂在里面,清清寡寡的汤水便洁白浓酽起来,成了一碗有色有味的汤汁。
放学回家,我拿把镰刀,挽个篮子在臂弯里,到田埂地头打猪草,趁机偷剥了蚕豆藏在篮子底,回来用针线穿成一串珠子丢在汤罐里煮了,上学路上,我颈垂珠串,学校未到,珠子早成了腹中物。
五月底,菜籽黄了,麦子熟了,豆角老了,蚕豆硬了皮乌了嘴,农家最忙的时节到了。农人忙里偷空把豆秸拔了,铺在地上,毒日头晒上几天,豆颗儿便脱壳而出。
夏天的傍晚,煮好了晚饭粥,我便赶忙着炒蚕豆。蚕豆皮两面微焦,发出“砰砰”的声音时,我赶紧盛起半碗放在一边,再舀起一瓢热水倒入锅中,搁两勺盐,盖了锅盖,闷上半个时辰。起锅了,拍上几瓣蒜粒,倒几滴香油,那蒜味焦香的豆子很快便让一盆凉粥见底,比那五香烂蚕豆不知香了多少。门前的凉床上,晚风习习,蛙声阵阵,口嚼余香,燥热的身心平静下来,好一个惬意的晚上。
那半碗干炒蚕豆最好打发时间了。抓两把在衣袋里,上学路上嘴里咯咯嘣嘣,喂饱了少年饥饿的馋虫。课间拿蚕豆抓子儿、猜子儿那是孩子间的输赢小赌,给少年生活增添了不少趣味。
邻居七十岁的德标老头馋酒,每顿两小盅雷打不动,酒菜并不讲究,一瓶大麦烧、一把硬蚕豆或黄豆是标配。路过的人戏谑道:“老头子,不要把牙嚼坏了。”老头不动声色,不紧不慢,抿一口酒,丢一颗蚕豆在嘴里,咯嘣一声,真担心他那一嘴历经沧桑的老牙突然自殉,他却一脸自得地扬起山羊胡:“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哉!”
村里的麦场上隔个半月一月都要放露天电影,孩子最是兴奋,和鲁迅的《社戏》里迅哥儿跟着一帮孩子乘船看戏差不多,但不同的是电影比唱戏好玩,他们偷煮蚕豆,我们不用,揣满一衣袋的干炒蚕豆,拎个小板凳,看电影。有部电影《柳堡的故事》,插曲很好听,叫作《九九艳阳天》:“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蚕豆花儿香啊,麦苗儿鲜……”柳堡就在几十里外的宝应,离我老家并不太远。熟悉的场景,动人的爱情,惹得庄上的姑娘大婶们追到邻近村子里反复看了几遍,从此,她们有事没事嘴里都哼唱着这歌的调调儿。有时走晚路,偶尔还会听到麦田油菜地里飘来的细细歌声,那沾着露水的蚕豆花香,湿漉漉地徘徊在有点忧伤的夜色里。
今天走过超市,超市的喇叭里传来了那熟悉的旋律,一种感觉和记忆顿时从心底被唤醒,四月了,又该是吃蚕豆的时候了,明天得上街去找找哪里有豆角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