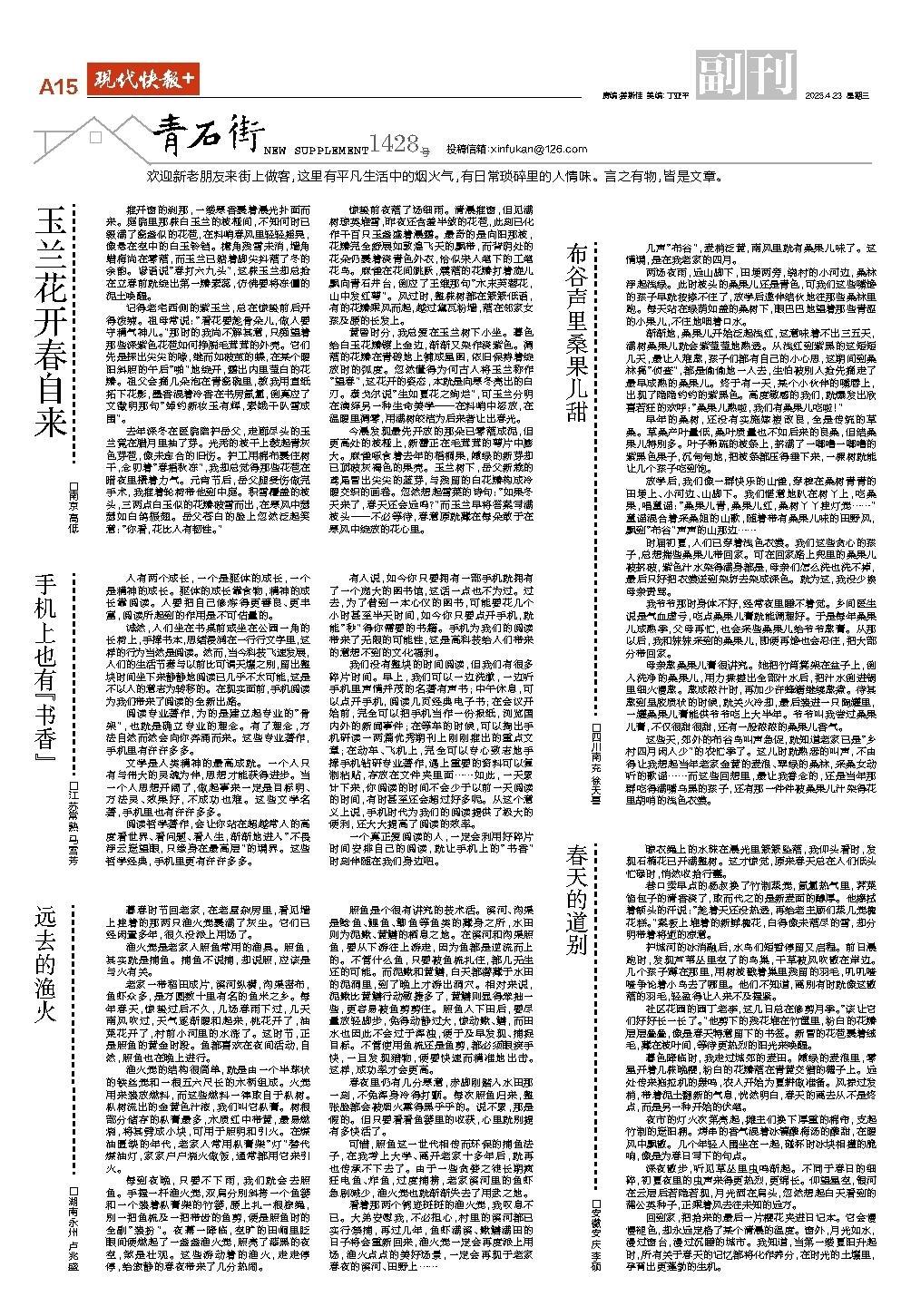□南京 高低
推开窗的刹那,一缕寒香裹着晨光扑面而来。庭院里那株白玉兰的枝桠间,不知何时已缀满了瓷盏似的花苞,在料峭春风里轻轻摇晃,像悬在空中的白玉铃铛。檐角残雪未消,墙角蜡梅尚在零落,而玉兰已踮着脚尖抖落了冬的余韵。谚语说“春打六九头”,这株玉兰却总抢在立春前就绽出第一瓣素蕊,仿佛要将冻僵的泥土唤醒。
记得老宅西侧的紫玉兰,总在惊蛰前后开得泼辣。祖母常说:“看花要趁骨朵儿,做人要守精气神儿。”那时的我尚不解其意,只痴望着那些深紫色花苞如何挣脱毛茸茸的外壳。它们先是探出尖尖的喙,继而如破茧的蝶,在某个暖阳斜照的午后“啪”地绽开,露出内里莹白的花瓣。祖父会摘几朵泡在青瓷碗里,教我用宣纸拓下花影,墨香混着冷香在书房氤氲,倒真应了文徵明那句“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
去年深冬在医院陪护岳父,走廊尽头的玉兰竟在腊月里抽了芽。光秃的枝干上鼓起青灰色芽苞,像未愈合的旧伤。护工用棉布裹住树干,念叨着“春捂秋冻”,我却总觉得那些花苞在暗夜里攒着力气。元宵节后,岳父腿受伤做完手术,我推着轮椅带他到中庭。积雪覆盖的枝头,三两点白玉似的花瓣破雪而出,在寒风中瑟瑟如白鸽振翅。岳父苍白的脸上忽然泛起笑意:“你看,花比人有韧性。”
惊蛰前夜落了场细雨。清晨推窗,但见满树琼英堆雪,昨夜还含羞半敛的花苞,此刻已化作千百只玉盏盛着晨露。最奇的是向阳那枝,花瓣完全舒展如敦煌飞天的飘带,而背阴处的花朵仍裹着淡青色外衣,恰似宋人笔下的工笔花鸟。麻雀在花间跳跃,震落的花瓣打着旋儿飘向青石井台,倒应了王维那句“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风过时,整株树都在簌簌低语,有的花瓣乘风而起,越过黛瓦粉墙,落在邻家女孩及腰的长发上。
黄昏时分,我总爱在玉兰树下小坐。暮色给白玉花瓣镀上金边,渐渐又染作淡紫色。凋落的花瓣在青砖地上铺成星图,依旧保持着绽放时的弧度。忽然懂得为何古人将玉兰称作“望春”,这花开的姿态,本就是向寒冬亮出的白刃。泰戈尔说“生如夏花之绚烂”,可玉兰分明在演绎另一种生命美学——在料峭中怒放,在温暖里凋零,用满树皎洁为后来者让出春光。
今晨发现最先开放的那朵已零落成泥,但更高处的枝桠上,新蕾正在毛茸茸的萼片中膨大。麻雀啄食着去年的梧桐果,嫩绿的新芽却已顶破灰褐色的果壳。玉兰树下,岳父新栽的鸢尾冒出尖尖的蓝芽,与残留的白花瓣构成冷暖交织的画卷。忽然想起雪莱的诗句:“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而玉兰早将答案写满枝头——不必等待,春意原就藏在每朵敢于在寒风中绽放的花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