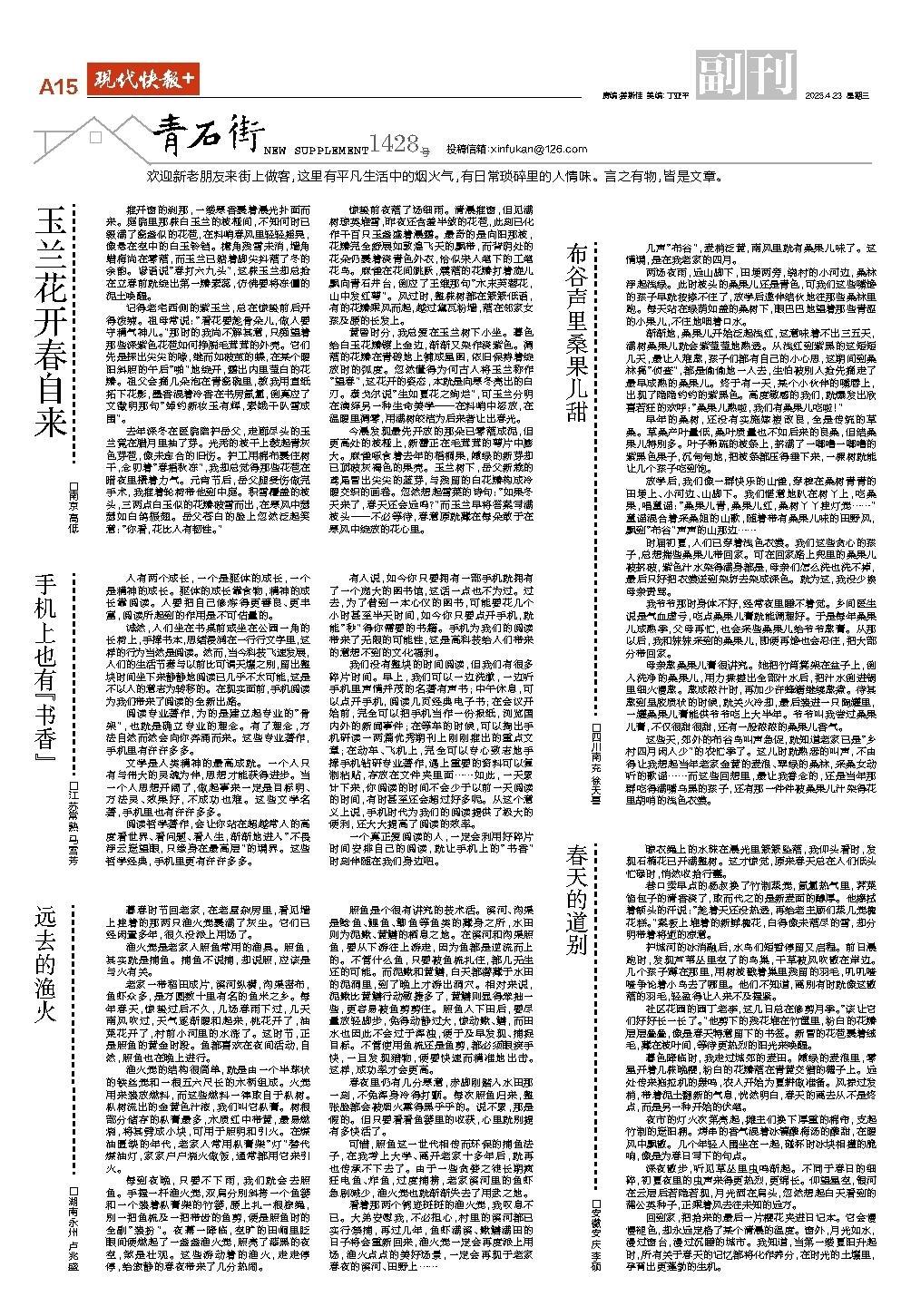□四川南充 徐天喜
几声“布谷”,麦梢泛黄,南风里就有桑果儿味了。这情境,是在我老家的四月。
两场夜雨,远山脚下,田埂两旁,绕村的小河边,桑林浮起浅绿。此时枝头的桑果儿还是青色,可我们这些嘴馋的孩子早就按捺不住了,放学后邀伴结伙地往那些桑林里跑。每天站在绿荫如盖的桑树下,眼巴巴地望着那些青涩的小果儿,不住地咽着口水。
渐渐地,桑果儿开始泛起浅红,这意味着不出三五天,满树桑果儿就会紫莹莹地熟透。从浅红到紫黑的这短短几天,最让人难熬,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小心思,这期间到桑林搞“侦查”,都是偷偷地一人去,生怕被别人抢先摘走了最早成熟的桑果儿。终于有一天,某个小伙伴的嘴唇上,出现了隐隐约约的紫黑色。高度敏感的我们,就爆发出欣喜若狂的欢呼:“桑果儿熟啦,我们有桑果儿吃啦!”
早年的桑树,还没有实施嫁接改良,全是传统的草桑。草桑产叶量低,桑叶质量也不如后来的良桑,但结桑果儿特别多。叶子稀疏的枝条上,挤满了一嘟噜一嘟噜的紫黑色果子,沉甸甸地,把枝条都压得垂下来,一棵树就能让几个孩子吃到饱。
放学后,我们像一群快乐的山雀,穿梭在桑树青青的田埂上、小河边、山脚下。我们惬意地趴在树丫上,吃桑果,唱童谣:“桑果儿青,桑果儿红,桑树丫丫挂灯笼……”童谣混合着采桑姐的山歌,随着带有桑果儿味的田野风,飘到“布谷”声声的山那边……
时届初夏,人们已穿着浅色衣裳。我们这些贪心的孩子,总想揣些桑果儿带回家。可在回家路上兜里的桑果儿被挤破,紫色汁水染得满身都是,母亲们怎么洗也洗不掉,最后只好把衣裳送到染坊去染成深色。就为这,我没少挨母亲责骂。
我爷爷那时身体不好,经常夜里睡不着觉。乡间医生说是气血虚亏,吃点桑果儿膏就能调理好。于是每年桑果儿成熟季,父母再忙,也会采些桑果儿给爷爷熬膏。从那以后,我和妹妹采到的桑果儿,即便再馋也会忍住,把大部分带回家。
母亲熬桑果儿膏很讲究。她把竹筲箕架在盆子上,倒入洗净的桑果儿,用力揉搓出全部汁水后,把汁水倒进锅里细火慢熬。熬成浓汁时,再加少许蜂糖继续熬煮。待其熬到呈胶质状的时候,就关火冷却,最后装进一只陶罐里,一罐桑果儿膏能供爷爷吃上大半年。爷爷叫我尝过桑果儿膏,不仅很甜很甜,还有一股浓浓的桑果儿香气。
这些天,郊外的布谷鸟叫声急促,就知道老家已是“乡村四月闲人少”的农忙季了。这儿时就熟悉的叫声,不由得让我想起当年老家金黄的麦浪、翠绿的桑林,采桑女动听的歌谣……而这些回想里,最让我眷念的,还是当年那群吃得满嘴乌黑的孩子,还有那一件件被桑果儿汁染得花里胡哨的浅色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