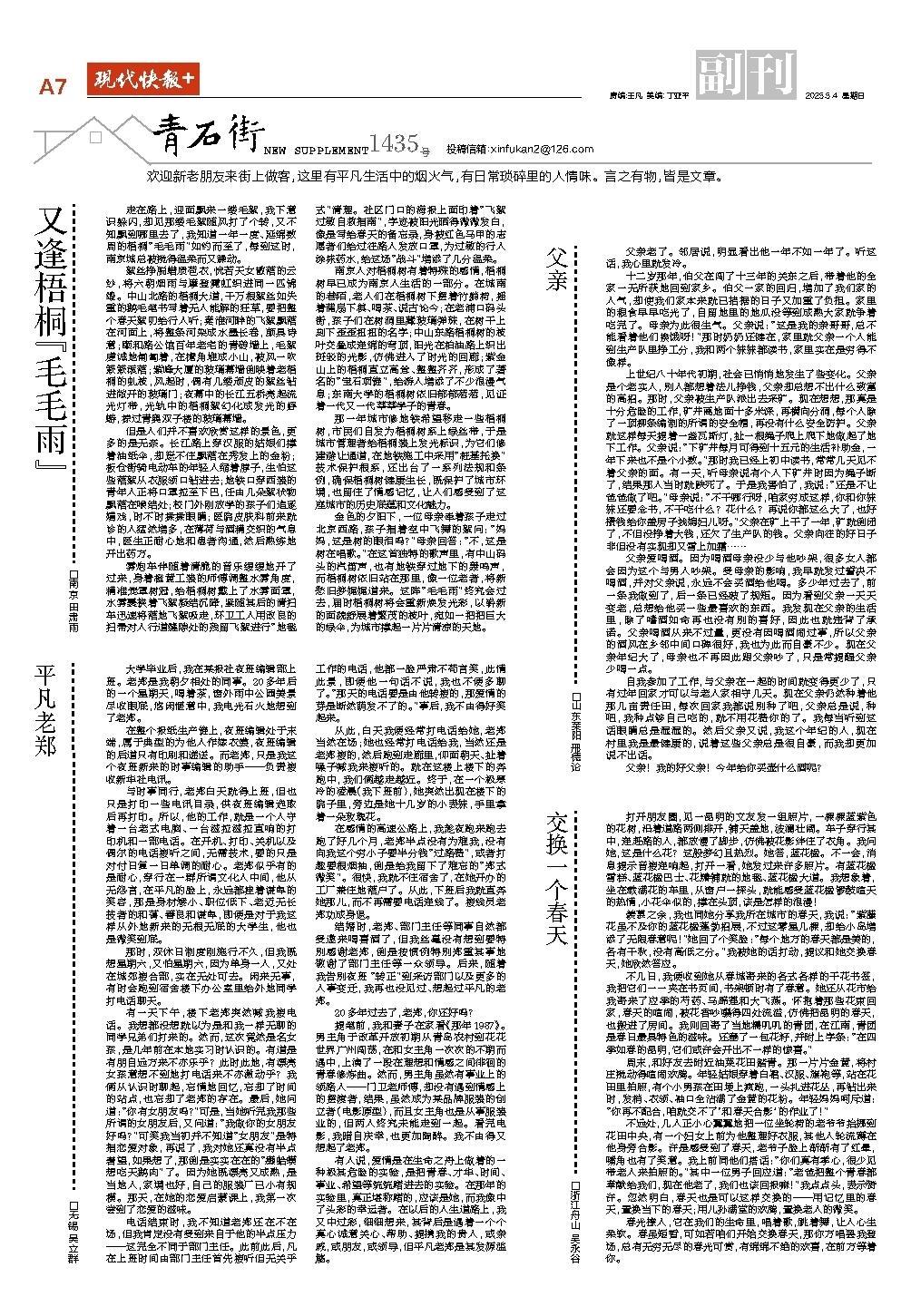□南京 田肃雨
走在路上,迎面飘来一缕毛絮,我下意识躲闪,却见那缕毛絮随风打了个转,又不知飘到哪里去了,我知道一年一度、延绵数周的梧桐“毛毛雨”如约而至了,每到这时,南京城总被搅得温柔而又躁动。
絮丝挣脱蜡质苞衣,恍若天女散落的云纱,将六朝烟雨与摩登霓虹织进同一匹锦缎。中山北路的梧桐大道,千万根絮丝如失重的鹅毛笔书写着无人能解的狂草,要把整个春天絮叨给行人听;秦淮河畔的飞絮飘落在河面上,将整条河染成水墨长卷,颇具诗意;颐和路公馆百年老宅的青砖墙上,毛絮虔诚地匍匐着,在檐角堆成小山,被风一吹簌簌滚落;紫峰大厦的玻璃幕墙倒映着老梧桐的虬枝,风起时,偶有几缕顽皮的絮丝钻进敞开的玻璃门;夜幕中的长江五桥亮起流光灯带,光轨中的梧桐絮幻化成发光的蜉蝣,掠过青奥双子楼的玻璃幕墙。
但是人们并不喜欢欣赏这样的景色,更多的是无奈。长江路上穿汉服的姑娘们撑着油纸伞,却遮不住飘落在秀发上的金粉;板仓街骑电动车的年轻人缩着脖子,生怕这些落絮从衣服领口钻进去;地铁口穿西装的青年人正将口罩拉至下巴,任由几朵絮状物飘落在喉结处;校门外刚放学的孩子们追逐嬉戏,时不时揉揉眼睛;医院皮肤科前来就诊的人猛然增多,在薄荷与酒精交织的气息中,医生正耐心地和患者沟通,然后熟练地开出药方。
雾炮车伴随着清脆的音乐缓缓地开了过来,身着橙黄工装的师傅调整水雾角度,精准笼罩树冠,给梧桐树戴上了水雾面罩,水雾裹挟着飞絮凝结沉降,紧随其后的清扫车迅速将落地飞絮吸走,环卫工人用改良的扫帚对人行道缝隙处的残留飞絮进行“地毯式”清理。社区门口的海报上面印着“飞絮过敏自救指南”,字迹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白,像是写给春天的备忘录,身披红色马甲的志愿者们给过往路人发放口罩,为过敏的行人涂抹药水,给这场“战斗”增添了几分温柔。
南京人对梧桐树有着特殊的感情,梧桐树早已成为南京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城南的巷陌,老人们在梧桐树下摆着竹躺椅,摇着蒲扇下棋、喝茶、说古论今;在老浦口码头街,孩子们在树洞里藏玻璃弹珠,在树干上刻下歪歪扭扭的名字;中山东路梧桐树的枝叶交叠成连绵的穹顶,阳光在柏油路上织出斑驳的光影,仿佛进入了时光的回廊;紫金山上的梧桐直立高耸、整整齐齐,形成了著名的“宝石项链”,给游人增添了不少浪漫气息;东南大学的梧桐树依旧郁郁葱葱,见证着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的青春。
那一年城市修地铁希望移走一些梧桐树,市民们自发为梧桐树系上绿丝带,于是城市管理者给梧桐装上发光标识,为它们修建避让通道,在地铁施工中采用“桩基托换”技术保护根系,还出台了一系列法规和条例,确保梧桐树健康生长,既保护了城市环境,也留住了情感记忆,让人们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
金色的夕阳下,一位母亲牵着孩子走过北京西路,孩子指着空中飞舞的絮问:“妈妈,这是树的眼泪吗?”母亲回答:“不,这是树在唱歌。”在这首独特的歌声里,有中山码头的汽笛声,也有地铁穿过地下的轰鸣声,而梧桐树依旧站在那里,像一位老者,将新愁旧梦娓娓道来。这阵“毛毛雨”终究会过去,届时梧桐树将会重新焕发光彩,以崭新的面貌舒展着繁茂的枝叶,宛如一把把巨大的绿伞,为城市撑起一片片清凉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