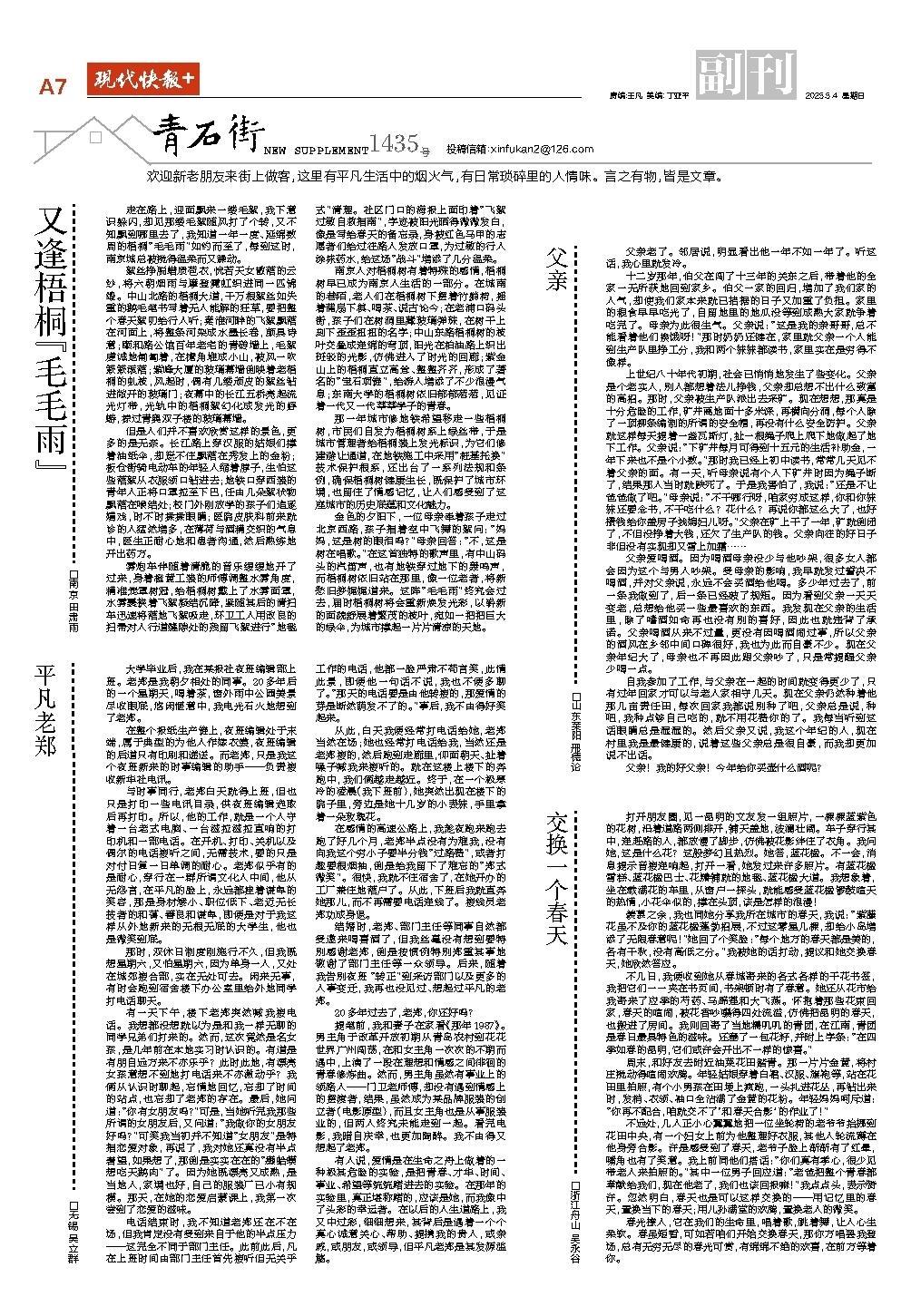□无锡 吴立群
大学毕业后,我在某报社夜班编辑部上班。老郑是我朝夕相处的同事。20多年后的一个星期天,喝着茶,窗外雨中公园美景尽收眼底,悠闲惬意中,我电光石火地想到了老郑。
在整个报纸生产链上,夜班编辑处于末端,属于典型的为他人作嫁衣裳,夜班编辑的后道只有印刷和递送。而老郑,只是我这个夜班新来的时事编辑的助手——负责接收新华社电讯。
与时事同行,老郑白天就得上班,但也只是打印一些电讯目录,供夜班编辑选取后再打印。所以,他的工作,就是一个人守着一台老式电脑、一台滋拉滋拉直响的打印机和一部电话。在开机、打印、关机以及偶尔的电话接听之间,无需技术,要的只是对付日复一日单调的耐心。老郑似乎有的是耐心,穿行在一群所谓文化人中间,他从无怨言,在平凡的脸上,永远都挂着谦卑的笑容,那是身材矮小、职位低下、老迈无长技者的和蔼、善良和谦卑,即便是对于我这样从外地新来的无根无底的大学生,他也是微笑到底。
那时,双休日制度刚施行不久,但我既想星期六,又怕星期六,因为单身一人,又处在城郊接合部,实在无处可去。闲来无事,有时会跑到宿舍楼下办公室里给外地同学打电话聊天。
有一天下午,楼下老郑突然喊我接电话。我想都没想就以为是和我一样无聊的同学兄弟们打来的。然而,这次竟然是名女孩,是几年前在本地实习时认识的。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此时此地,有漂亮女孩意想不到地打电话来不亦激动乎?我俩从认识时聊起,忘情地回忆,忘却了时间的站点,也忘却了老郑的存在。最后,她问道:“你有女朋友吗?”可是,当她听完我那些所谓的女朋友后,又问道:“我做你的女朋友好吗?”可笑我当初并不知道“女朋友”是特指恋爱对象,再说了,我对她还真没有半点奢望,如果想了,那倒是实实在在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因为她既漂亮又成熟,是当地人,家境也好,自己的服装厂已小有规模。那天,在她的恋爱启蒙课上,我第一次尝到了恋爱的滋味。
电话结束时,我不知道老郑还在不在场,但我肯定没有受到来自于他的半点压力——这完全不同于部门主任。此前此后,凡在上班时间由部门主任首先接听但无关乎工作的电话,他都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此情此景,即便他一句话不说,我也不便多聊了。“那天的电话要是由他转接的,那爱情的芽是断然萌发不了的。”事后,我不由得好笑起来。
从此,白天我便经常打电话给她,老郑当然在场;她也经常打电话给我,当然还是老郑接的,然后跑到走廊里,仰面朝天、扯着嗓子喊我来接听的。就在这楼上楼下的奔跑中,我们俩越走越近。终于,在一个极寒冷的凌晨(我下班前),她突然出现在楼下的院子里,旁边是她十几岁的小表妹,手里拿着一朵玫瑰花。
在感情的高速公路上,我趁夜跑来跑去跑了好几个月,老郑半点没有为难我,没有向我这个穷小子要半分钱“过路费”,或者打趣要根烟抽,倒是给我留下了难忘的“郑式微笑”。很快,我就不住宿舍了,在她开办的工厂兼住地落户了。从此,下班后我就直奔她那儿,而不再需要电话连线了。接线员老郑功成身退。
结婚时,老郑、部门主任等同事自然都受邀来喝喜酒了,但我丝毫没有想到要特别感谢老郑,倒是按惯例特别郑重其事地敬谢了部门主任等一众领导。后来,随着我告别夜班 “转正”到采访部门以及更多的人事变迁,我再也没见过、想起过平凡的老郑。
20多年过去了,老郑,你还好吗?
提笔前,我和妻子在家看《那年1987》。男主角于改革开放初期从青岛农村到花花世界广州闯荡,在和女主角一次次的不期而遇中,上演了一段在理想和情感之间徘徊的青春修炼曲。然而,男主角虽然有事业上的领路人——门卫老师傅,却没有遇到情感上的摆渡者,结果,虽然成为某品牌服装的创立者(电影原型),而且女主角也是从事服装业的,但两人终究未能走到一起。看完电影,我暗自庆幸,也更加陶醉。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老郑。
有人说,爱情是在生命之舟上做着的一种极其危险的实验,是把青春、才华、时间、事业、希望等统统赌进去的实验。在那年的实验里,真正堪称赌的,应该是她,而我像中了头彩的幸运者。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又中过彩,细细想来,其背后是遇着一个个真心诚意关心、帮助、提携我的贵人,或亲戚,或朋友,或领导,但平凡老郑是其发源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