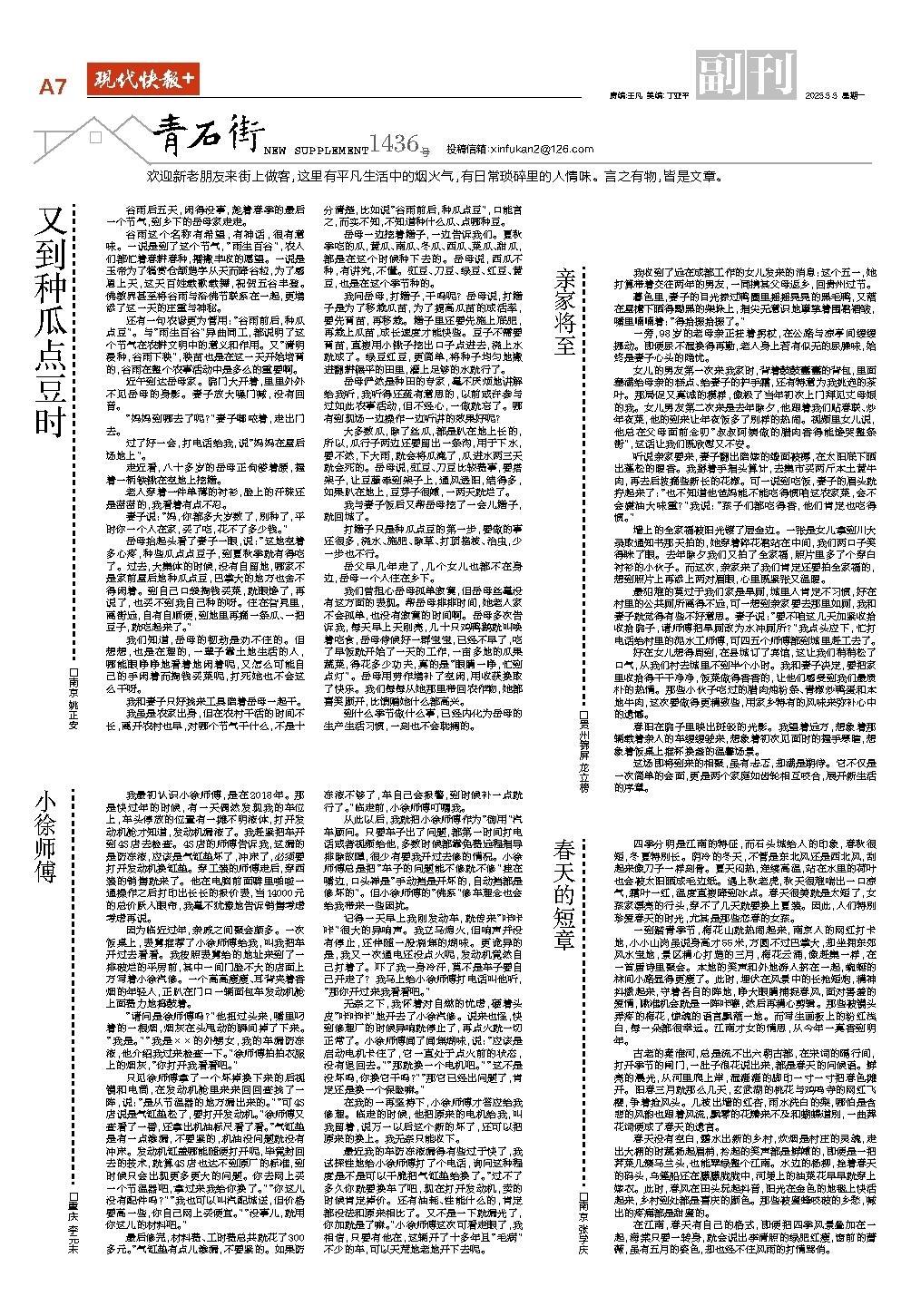□贵州锦屏 龙立榜
我收到了远在成都工作的女儿发来的消息:这个五一,她打算带着交往两年的男友,一同携其父母返乡,回贵州过节。
暮色里,妻子的目光掠过鸭圈里摇摇晃晃的黑毛鸭,又落在屋檐下晒得黝黑的柴垛上,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围裙褶皱,嘴里喃喃着:“得拾掇拾掇了。”
一旁,98岁的老母亲正拄着拐杖,在公路与凉亭间缓缓挪动。即便尿不湿换得再勤,老人身上若有似无的尿臊味,始终是妻子心头的隐忧。
女儿的男友第一次来我家时,背着鼓鼓囊囊的背包,里面塞满给母亲的糕点、给妻子的护手霜,还有特意为我挑选的茶叶。那局促又真诚的模样,像极了当年初次上门拜见丈母娘的我。女儿男友第二次来是去年除夕,他跟着我们贴春联、炒年夜菜,他的到来让年夜饭多了别样的热闹。视频里女儿说,他总在父母面前念叨“叔叔阿姨做的腊肉香得能馋哭整条街”,这话让我们既欣慰又不安。
听说亲家要来,妻子翻出陪嫁的缎面被褥,在太阳底下晒出蓬松的暖香。我掰着手指头算计,去集市买两斤本土黄牛肉,再去后坡摘些新长的花椒。可一说到吃饭,妻子的眉头就拧起来了:“也不知道他爸妈能不能吃得惯咱这农家菜,会不会嫌油大味重?”我说:“孩子们都吃得香,他们肯定也吃得惯。”
墙上的全家福被阳光镀了层金边。一张是女儿拿到川大录取通知书那天拍的,她穿着碎花裙站在中间,我们两口子笑得眯了眼。去年除夕我们又拍了全家福,照片里多了个穿白衬衫的小伙子。而这次,亲家来了我们肯定还要拍全家福的,想到照片上再添上两对眉眼,心里既紧张又温暖。
最犯难的莫过于我们家是旱厕,城里人肯定不习惯,好在村里的公共厕所离得不远,可一想到亲家要去那里如厕,我和妻子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妻子说:“要不咱这几天加紧收拾收拾院子,请师傅把旱厕改为水冲厕所?”我点头应下,忙打电话给村里的泥水工师傅,可四五个师傅都到城里赶工去了。
好在女儿想得周到,在县城订了宾馆,这让我们稍稍松了口气,从我们村去城里不到半个小时。我和妻子决定,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饭菜做得香香的,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最质朴的热情。那些小伙子吃过的腊肉炖粉条、青椒炒鸭蛋和本地牛肉,这次要做得更精致些,用家乡特有的风味来弥补心中的遗憾。
春阳在院子里映出斑驳的光影。我望着远方,想象着那辆载着亲人的车缓缓驶来,想象着初次见面时的握手寒暄,想象着饭桌上推杯换盏的温馨场景。
这场即将到来的相聚,虽有忐忑,却满是期待。它不仅是一次简单的会面,更是两个家庭如齿轮相互咬合,展开新生活的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