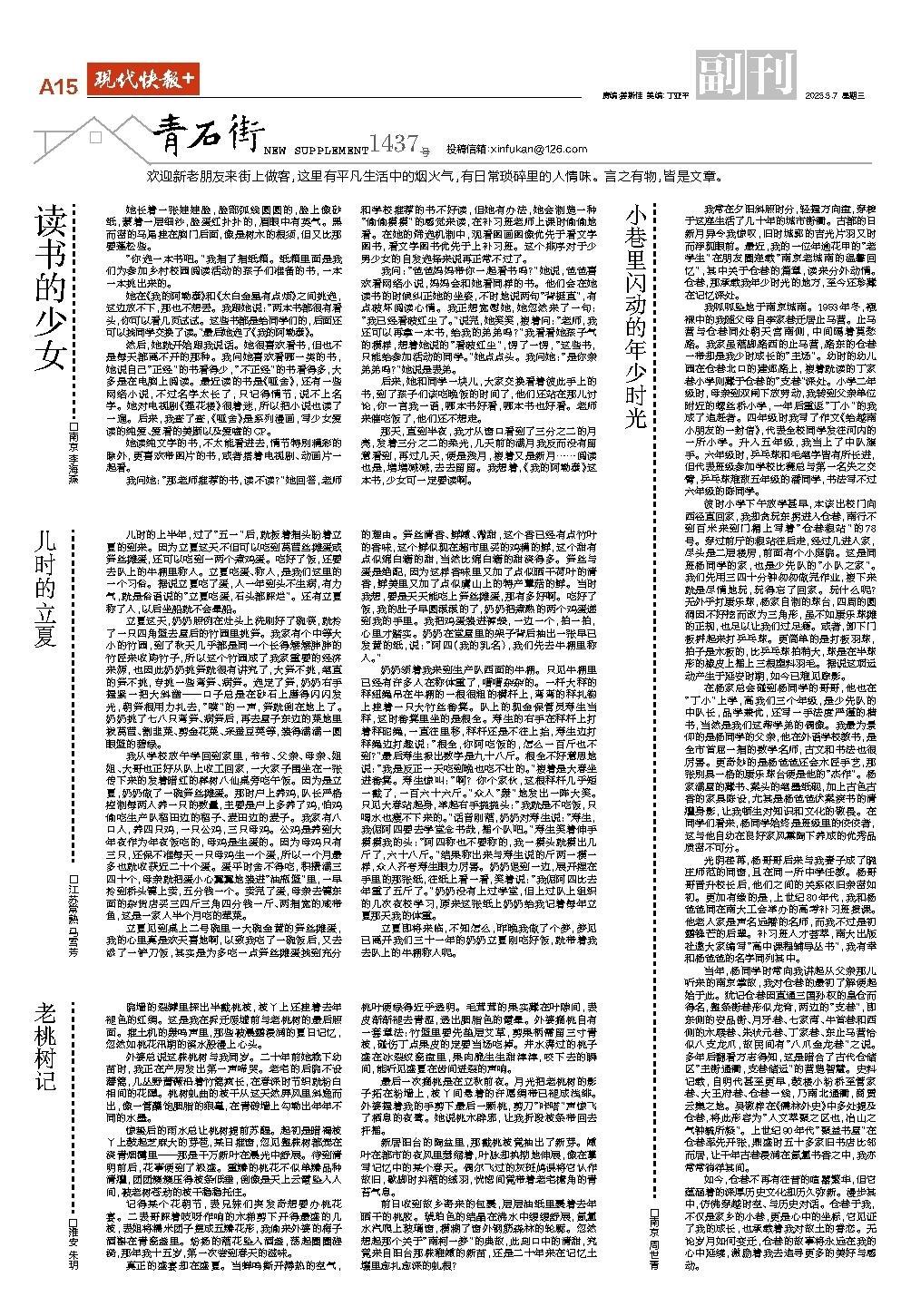□淮安 朱玥
院墙的裂罅里探出半截桃枝,枝丫上还挂着去年褪色的红绸。这是我在拆迁废墟前与老桃树的最后照面。推土机的轰鸣声里,那些被晨露浸润的夏日记忆,忽然如桃花汛期的溪水般漫上心头。
外婆总说这株桃树与我同岁。二十年前她栽下幼苗时,我正在产房发出第一声啼哭。老宅的后院不设藩篱,几丛野蔷薇沿着竹篱疯长,在春深时节织就粉白相间的花障。桃树虬曲的枝干从这天然屏风里斜逸而出,像一管蘸饱胭脂的狼毫,在青砖墙上勾勒出年年不同的水墨。
惊蛰后的雨水总让桃树提前苏醒。起初是暗褐枝丫上鼓起芝麻大的芽苞,某日推窗,忽见整株树都笼在淡青烟霭里——那是千万新叶在晨光中舒展。待到清明前后,花事便到了极盛。重瓣的桃花不似单瓣品种清癯,团团簇簇压得枝条低垂,倒像是天上云霞坠入人间,被老树苍劲的枝干稳稳托住。
记得某个花朝节,表兄妹们突发奇想要办桃花宴。二表哥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梯剪下开得最盛的几枝,表姐将糯米团子摆成五瓣花形,我偷来外婆的梅子酒斟在青瓷盏里。纷扬的落花坠入酒盏,荡起圈圈涟漪,那年我十五岁,第一次尝到春天的滋味。
真正的盛宴却在盛夏。当蝉鸣撕开溽热的空气,桃叶便绿得近乎透明。毛茸茸的果实藏在叶隙间,表皮渐渐褪去青涩,透出胭脂色的霞晕。外婆摘桃自有一套章法:竹篮里要先垫层艾草,剪果柄需留三寸青枝,碰伤丁点果皮的定要当场吃掉。井水湃过的桃子盛在冰裂纹瓷盘里,果肉脆生生甜津津,咬下去的瞬间,能听见盛夏在齿间迸裂的声响。
最后一次摘桃是在立秋前夜。月光把老桃树的影子拓在粉墙上,枝丫间悬着的许愿绸带已褪成浅绯。外婆握着我的手剪下最后一颗桃,剪刀“咔嗒”声惊飞了栖息的夜鹭。她说桃木辟邪,让我折段枝条带回去扦插。
新居阳台的陶盆里,那截桃枝竟抽出了新芽。嫩叶在都市的夜风里瑟缩着,叶脉却执拗地伸展,像在摹写记忆中的某个春天。偶尔飞过的灰斑鸠误将它认作故旧,歇脚时抖落的绒羽,恍惚间竟带着老宅檐角的青苔气息。
前日收到故乡寄来的包裹,层层油纸里裹着去年晒干的桃胶。琥珀色的结晶在沸水中缓缓舒展,氤氲水汽爬上玻璃窗,模糊了窗外钢筋森林的轮廓。忽然想起那个关于“南柯一梦”的典故,此刻口中的清甜,究竟来自阳台那株稚嫩的新苗,还是二十年来在记忆土壤里愈扎愈深的虬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