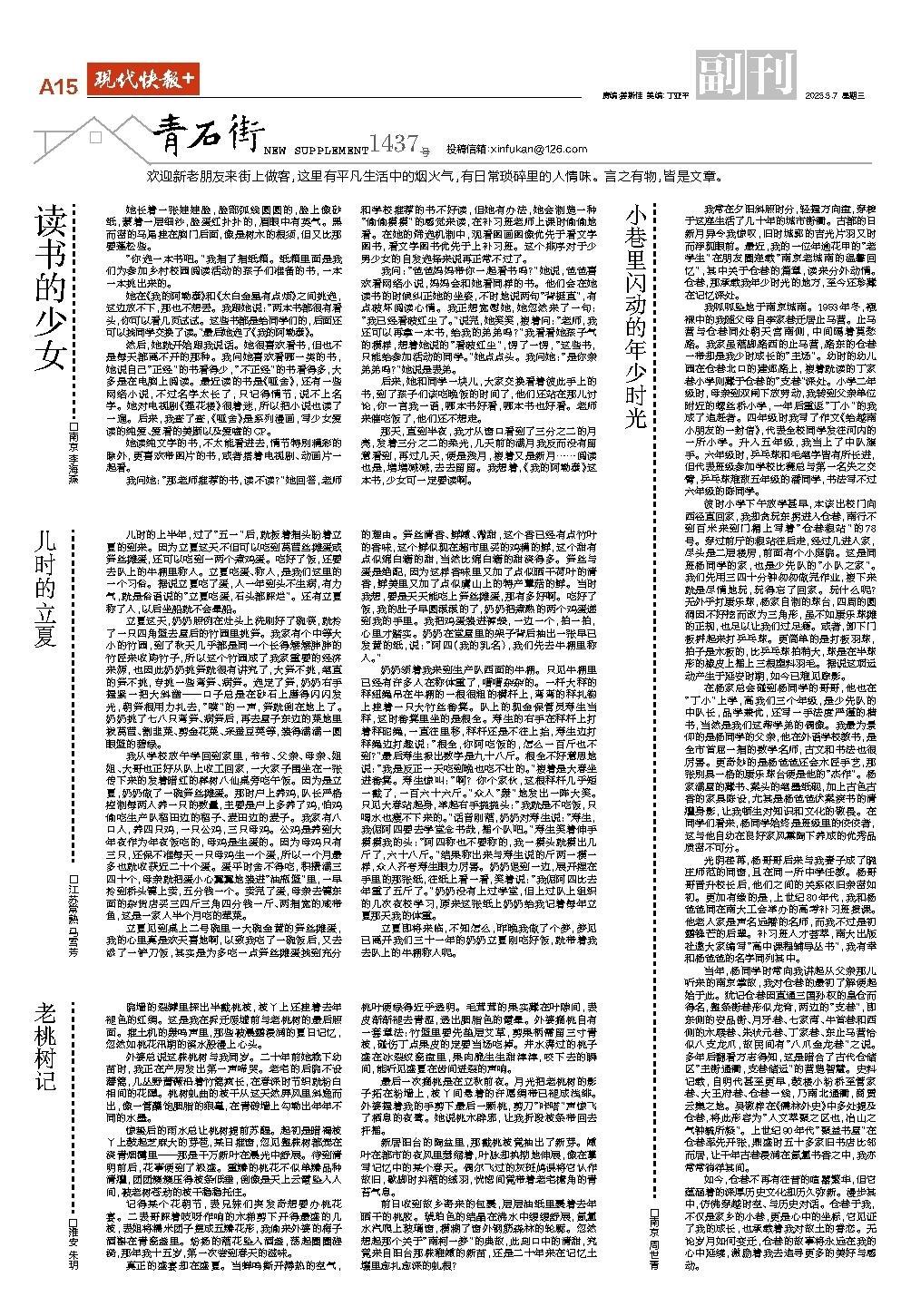□江苏常熟 马雪芳
儿时的上半年,过了“五一”后,就扳着指头盼着立夏的到来。因为立夏这天不但可以吃到莴苣丝摊蛋或笋丝摊蛋,还可以吃到一两个煮鸡蛋。吃好了饭,还要去队上的牛棚里称人。立夏吃蛋、称人,是我们这里的一个习俗。据说立夏吃了蛋,人一年到头不生病,有力气,就是俗语说的“立夏吃蛋,石头都踩烂”。还有立夏称了人,以后坐船就不会晕船。
立夏这天,奶奶照例在灶头上洗刷好了碗筷,就拎了一只四角篮去屋后的竹园里挑笋。我家有个中等大小的竹园,到了秋天几乎都是同一个长得矮矮胖胖的竹匠来收购竹子,所以这个竹园成了我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也因此奶奶挑笋就很有讲究了,大笋不挑,笔直的笋不挑,专挑一些弯笋、病笋。选定了笋,奶奶右手握紧一把大斜凿——口子总是在砂石上磨得闪闪发光,朝笋根用力扎去,“噗”的一声,笋就倒在地上了。奶奶挑了七八只弯笋、病笋后,再去屋子东边的菜地里拔莴苣、割韭菜、剪金花菜、采蚕豆荚等,装得满满一圆眼篮的碧绿。
我从学校放午学回到家里,爷爷、父亲、母亲、姐姐、大哥也正好从队上收工回家,一大家子围坐在一张传下来的发着暗红的榉树八仙桌旁吃午饭。因为是立夏,奶奶做了一碗笋丝摊蛋。那时户上养鸡,队长严格控制每两人养一只的数量,主要是户上多养了鸡,怕鸡偷吃生产队稻田边的稻子、麦田边的麦子。我家有八口人,养四只鸡,一只公鸡,三只母鸡。公鸡是养到大年夜作为年夜饭吃的,母鸡是生蛋的。因为母鸡只有三只,还保不准每天一只母鸡生一个蛋,所以一个月最多也就收获近二十个蛋。蛋平时舍不得吃,积攒满三四十个,母亲就把蛋小心翼翼地装进“油瓶篮”里,一早拎到桥头镇上卖,五分钱一个。卖完了蛋,母亲去镇东面的杂货店买三四斤三角四分钱一斤、两指宽的咸带鱼,这是一家人半个月吃的荤菜。
立夏见到桌上二号碗里一大碗金黄的笋丝摊蛋,我的心里真是欢天喜地啊,以致我吃了一碗饭后,又去添了一铲刀饭,其实是为多吃一点笋丝摊蛋找到充分的理由。笋丝清香、鲜嫩、微甜,这个香已经有点竹叶的香味,这个鲜似现在超市里买的鸡精的鲜,这个甜有点似绵白糖的甜,当然比绵白糖的甜淡得多。笋丝与蛋是绝配,因为这样香味里又加了点似晒干荷叶的清香,鲜美里又加了点似虞山上的特产蕈菇的鲜。当时我想,要是天天能吃上笋丝摊蛋,那有多好啊。吃好了饭,我的肚子早圆滚滚的了,奶奶把煮熟的两个鸡蛋递到我的手里。我把鸡蛋装进裤袋,一边一个,拍一拍,心里才踏实。奶奶在堂屋里的架子背后抽出一张早已发黄的纸,说:“阿四(我的乳名),我们先去牛棚里称人。”
奶奶领着我来到生产队西面的牛棚。只见牛棚里已经有许多人在称体重了,嘈嘈杂杂的。一杆大秤的秤纽绳吊在牛棚的一根很粗的横杆上,弯弯的秤扎钩上挂着一只大竹丝畚箕。队上的现金保管员寿生当秤,这时畚箕里坐的是根全。寿生的右手在秤杆上打着秤砣绳,一直往里移,秤杆还是不往上抬,寿生边打秤绳边打趣说:“根全,你阿吃饭的,怎么一百斤也不到?”最后寿生报出数字是九十八斤。根全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反正一天吃到晚也吃不壮的。”接着是大春坐进畚箕。寿生惊叫:“啊?你个家伙,这根秤杆几乎短一截了,一百六十六斤。”众人“轰”地发出一阵大笑。只见大春站起身,举起右手挠挠头:“我就是不吃饭,只喝水也瘦不下来的。”话音刚落,奶奶对寿生说:“寿生,我伲阿四要去学堂念书哉,插个队吧。”寿生笑着伸手摸摸我的头:“阿四称也不要称的,我一摸头就摸出几斤了,六十八斤。”结果称出来与寿生说的斤两一模一样,众人齐夸寿生眼力厉害。奶奶退到一边,展开捏在手里的那张纸,往纸上看一看,笑着说:“我伲阿四比去年重了五斤了。”奶奶没有上过学堂,但上过队上组织的几次夜校学习,原来这张纸上奶奶给我记着每年立夏那天我的体重。
立夏即将来临,不知怎么,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已离开我们三十一年的奶奶立夏刚吃好饭,就带着我去队上的牛棚称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