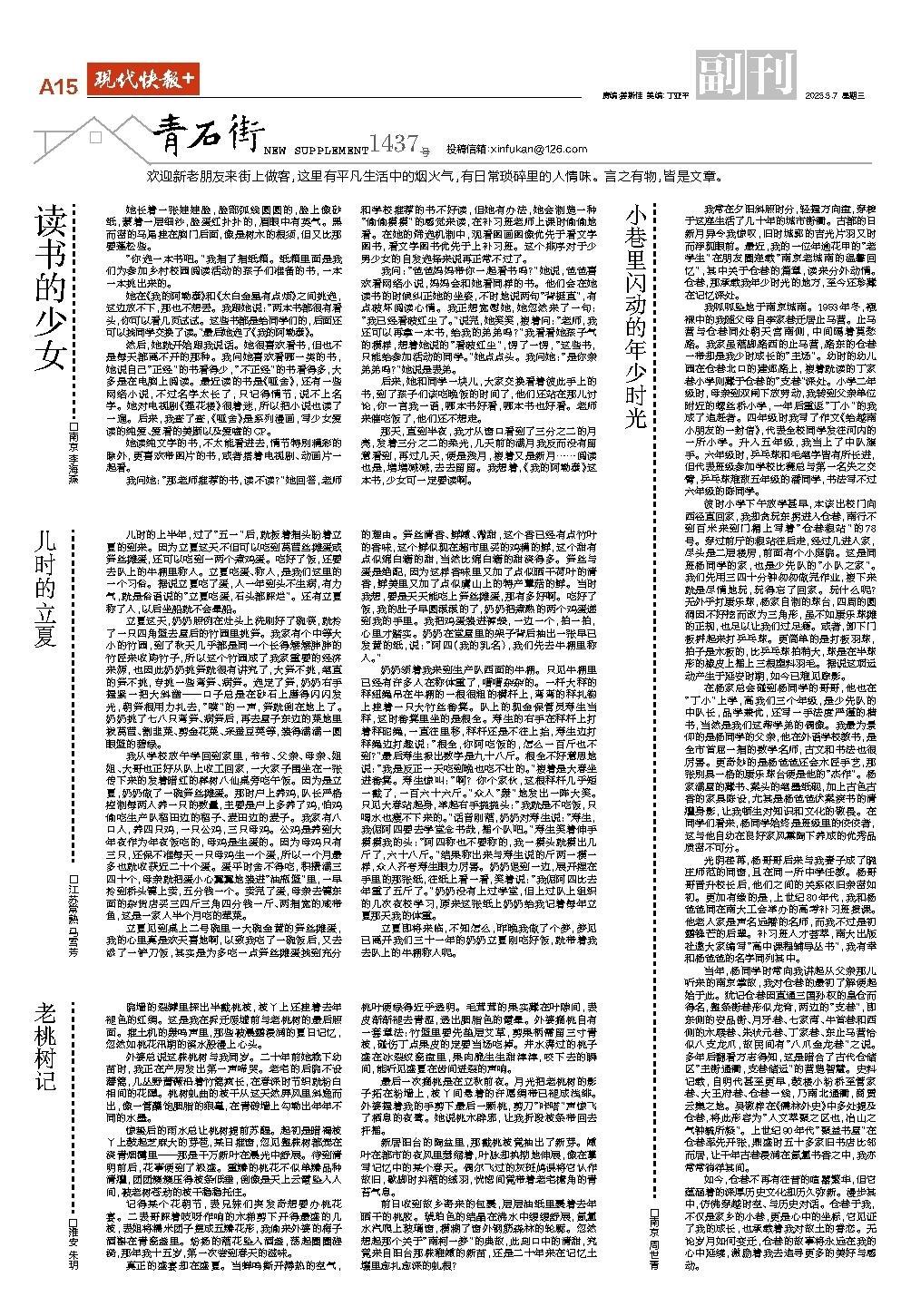□南京 周世青
我常在夕阳斜照时分,轻握方向盘,穿梭于这座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街衢。古都的日新月异令我惊叹,旧时城郭的吉光片羽又时而浮现眼前。最近,我的一位年逾花甲的“老学生”在朋友圈连载“南京老城南的温馨回忆”,其中关于仓巷的篇章,读来分外动情。仓巷,那承载我年少时光的地方,至今还珍藏在记忆深处。
我呱呱坠地于南京城南。1953年冬,襁褓中的我随父母自李家巷迁居止马营。止马营与仓巷同处朝天宫南侧,中间隔着莫愁路。我家虽落脚路西的止马营,路东的仓巷一带却是我少时成长的“主场”。幼时的幼儿园在仓巷北口的建邺路上,接着就读的丁家巷小学则藏于仓巷的“支巷”深处。小学二年级时,母亲到双闸下放劳动,我转到父亲单位附近的螺丝桥小学,一年后重返“丁小”的我成了追赶者。四年级时我写了作文《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代表全校同学发往河内的一所小学。升入五年级,我当上了中队旗手。六年级时,乒乓球和毛笔字皆有所长进,但代表班级参加学校比赛总与第一名失之交臂,乒乓球难敌五年级的潘同学,书法写不过六年级的陈同学。
彼时小学下午放学甚早,本该出校门向西径直回家,我却贪玩东拐进入仓巷,南行不到百米来到门楣上写着“仓巷粮站”的78号。穿过前厅的粮站往后走,经过几进人家,尽头是二层楼房,前面有个小庭院。这是同班杨同学的家,也是少先队的“小队之家”。我们先用三四十分钟匆匆做完作业,接下来就是尽情地玩,玩得忘了回家。玩什么呢?无外乎打康乐球,杨家自制的球台,四周的圆洞因不好挖而改为三角形,虽不如康乐球摊的正规,也足以让我们过足瘾。或者,卸下门板拼起来打乒乓球。更简单的是打板羽球,拍子是木板的,比乒乓球拍稍大,球是在半球形的橡皮上插上三根塑料羽毛。据说这项运动产生于延安时期,如今已难见踪影。
在杨家总会碰到杨同学的哥哥,他也在“丁小”上学,高我们三个年级,是少先队的中队长,品学兼优,还写一手法度严谨的楷书,当然是我们这帮学弟的偶像。我最为景仰的是杨同学的父亲,他在外语学校教书,是全市首屈一指的数学名师,古文和书法也很厉害。更奇妙的是杨爸爸还会木匠手艺,那张别具一格的康乐球台便是他的“杰作”。杨家满屋的藏书、案头的笔墨纸砚,加上古色古香的家具陈设,尤其是杨爸爸伏案疾书的清癯身影,让我顿生对知识和文化的敬畏。在同学们看来,杨同学始终是班级里的佼佼者,这与他自幼在良好家风熏陶下养成的优秀品质密不可分。
光阴荏苒,杨哥哥后来与我妻子成了晓庄师范的同窗,且在同一所中学任教。杨哥哥晋升校长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依旧亲密如初。更加有缘的是,上世纪80年代,我和杨爸爸同在南大工会举办的高考补习班授课。他老人家是声名远播的名师,而我不过是初露锋芒的后辈。补习班人才荟萃,南大出版社邀大家编写“高中课程辅导丛书”,我有幸和杨爸爸的名字同列其中。
当年,杨同学时常向我讲起从父亲那儿听来的南京掌故,我对仓巷的最初了解便起始于此。犹记仓巷因直通三国孙权的皇仓而得名,整条街巷形似龙脊,两边的“支巷”,即东侧的安品街、月牙巷、七家湾、牛首巷和西侧的木屐巷、朱状元巷、丁家巷、东止马营恰似八支龙爪,故民间有“八爪金龙巷”之说。多年后翻看方志得知,这是暗合了古代仓储区“主街通衢,支巷储运”的营造智慧。史料记载,自明代甚至更早,鼓楼小粉桥至管家巷、大王府巷、仓巷一线,乃南北通衢,商贾云集之地。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多处提及仓巷,将此形容为“人文萃聚之区也,冶山之气钟毓所凝”。上世纪90年代“聚益书屋”在仓巷率先开张,鼎盛时五十多家旧书店比邻而居,让千年古巷浸润在氤氲书香之中,我亦常常徜徉其间。
如今,仓巷不再有往昔的喧嚣繁华,但它蕴涵着的深厚历史文化却历久弥新。漫步其中,仿佛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仓巷于我,不仅是家乡的小巷,更是心中的坐标,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也承载着我对故土的眷恋。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仓巷的故事将永远在我的心中延续,激励着我去追寻更多的美好与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