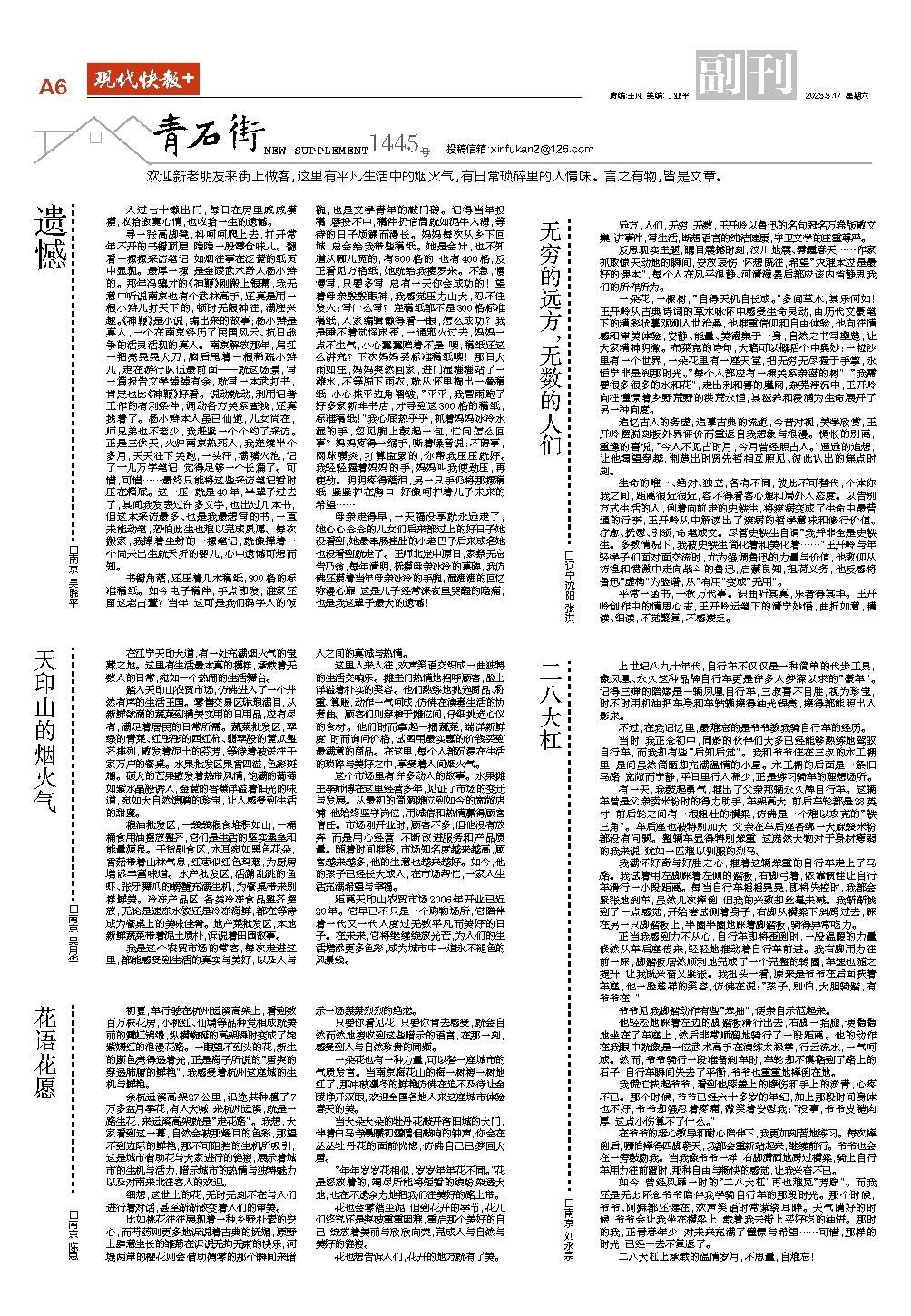□南京 吴晓平
人过七十懒出门,每日在房里戚戚摸摸,收拾寂寞心情,也收拾一生的遗憾。
寻一张高脚凳,抖呵呵爬上去,打开常年不开的书橱顶层,隐隐一股霉仓味儿。翻看一摞摞采访笔记,如烟往事在泛黄的纸页中显现。最厚一摞,是金陵武术奇人杨小辫的。那年冯骥才的《神鞭》刚搬上银幕,我无意中听说南京也有个武林高手,还真是用一根小辫儿打天下的,顿时无限神往,满腔兴趣。《神鞭》是小说,编出来的故事;杨小辫是真人,一个在南京经历了民国风云、抗日战争的活灵活现的真人。南京解放那年,肩扛一把亮晃晃大刀,脑后甩着一根稀疏小辫儿,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就这场景,写一篇报告文学绰绰有余,就写一本武打书,肯定也比《神鞭》好看。说动就动,利用记者工作的有利条件,调动各方关系查找,还真找着了。杨小辫本人虽已仙逝,儿女尚在,师兄弟也不老少,我赶紧一个个约了采访。正是三伏天,火炉南京热死人,我连续半个多月,天天往下关跑,一头汗,满嘴火泡,记了十几万字笔记,觉得足够一个长篇了。可惜,可惜……最终只能将这些采访笔记暂时压在箱底。这一压,就是40年,半辈子过去了,其间我发表过许多文字,也出过几本书,但这本采访最多、也是我最想写的书,一直未能动笔,恐怕此生也难以完成夙愿。每次搬家,我捧着尘封的一摞笔记,就像捧着一个尚未出生就夭折的婴儿,心中遗憾可想而知。
书橱角落,还压着几本稿纸,300格的标准稿纸。如今电子稿件,手点即发,谁家还留这老古董?当年,这可是我们码字人的饭碗,也是文学青年的敲门砖。记得当年投稿,屡投不中,稿件扔信筒就如泥牛入海,等待的日子烦躁而漫长。妈妈每次从乡下回城,总会给我带些稿纸。她是会计,也不知道从哪儿觅的,有500格的,也有400格,反正看见方格纸,她就给我搜罗来。不急,慢慢写,只要多写,总有一天你会成功的!望着母亲殷殷眼神,我感觉压力山大,忍不住发火:写什么写?连稿纸都不是300格标准稿纸,人家编辑懒得看一眼,怎么成功?我是睡不着觉怪床歪,一通邪火过去,妈妈一点不生气,小心翼翼赔着不是:噢,稿纸还这么讲究?下次妈妈买标准稿纸噢!那日大雨如注,妈妈突然回家,进门湿漉漉站了一滩水,不等脱下雨衣,就从怀里掏出一叠稿纸,小心抹平边角褶皱,“平平,我冒雨跑了好多家新华书店,才寻到这300格的稿纸,标准稿纸!”我心底热乎乎,抓着妈妈冰冷水湿的手,忽见腕上鼓起一包,忙问怎么回事?妈妈疼得一缩手,嘶着嗓音说:不碍事,网球膜炎,打算盘累的,你帮我压压就好。我轻轻握着妈妈的手,妈妈叫我使劲压,再使劲。明明疼得落泪,另一只手仍将那摞稿纸,紧紧护在胸口,好像呵护着儿子未来的希望……
母亲走得早,一天福没享就永远走了,她心心念念的儿女们后来都过上的好日子她没看到,她最牵肠挂肚的小老巴子后来成名她也没看到就走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每年清明,抚摸母亲冰冷的墓碑,我仿佛还摸着当年母亲冰冷的手腕,湿漉漉的回忆弥漫心扉,这是儿子经常深夜里哭醒的隐痛,也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