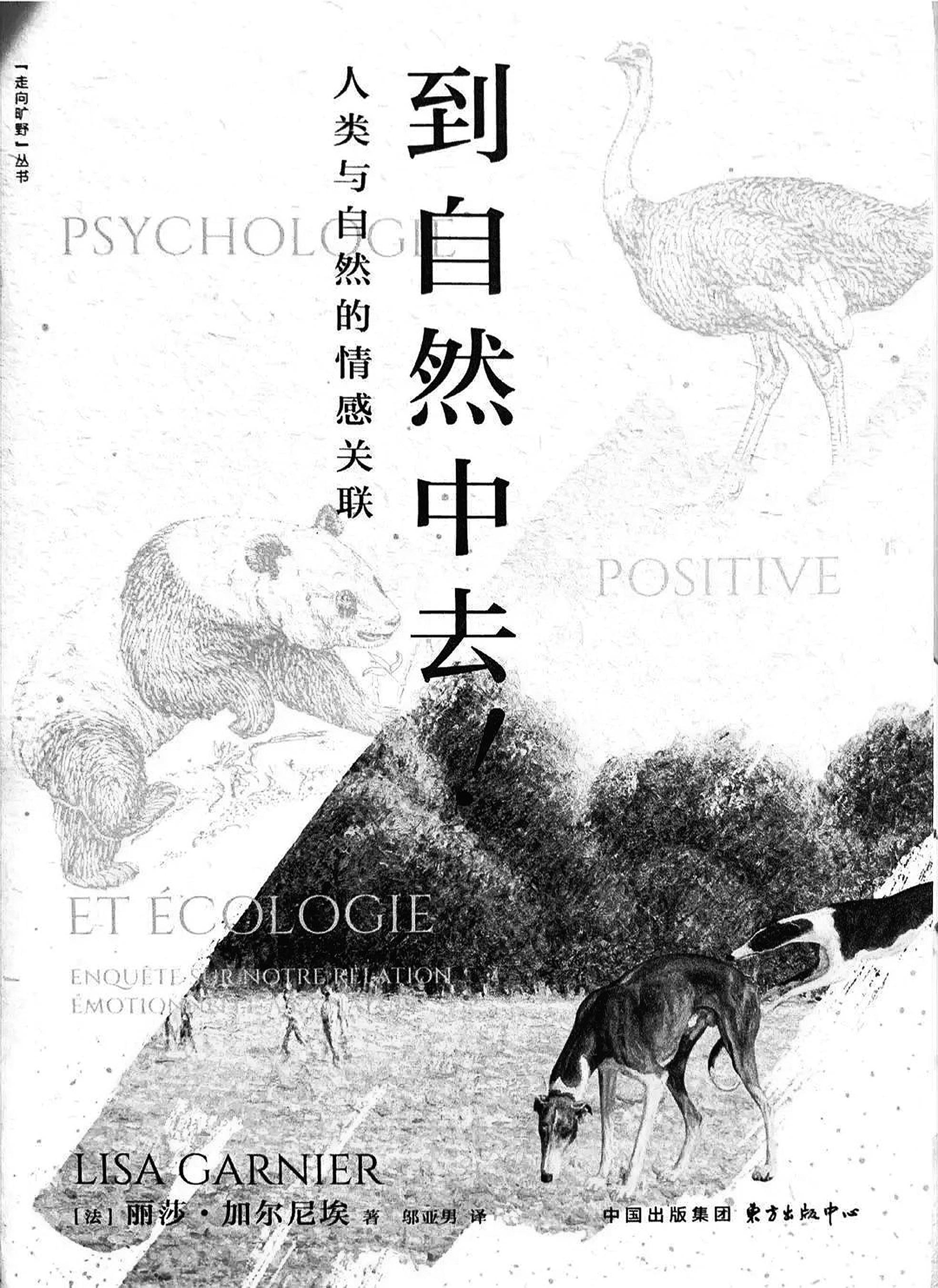□陆远
易洛魁人是生活在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东南部的印第安族群,这个部落延续着一项古老的传统——在召开长老会议时,总会有一名长老被指定代表狼发言。易洛魁人生活的北美地区是犬科动物主要的发源地之一,作为北美大陆分布最广泛的犬科动物,狼也是易洛魁部落最主要的图腾(就像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记录的那样)。在易洛魁人看来,狼与人相互依存、共同生活,人不是高高在上统摄一切的“万物之灵”,而是与自然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
在“文明世界”中生活的现代人,恐怕会对这样“愚昧”的行为不屑一顾,又或许视之为文化人类学的“标本”,小心翼翼圈养起来以供观瞻。不过,法国生物学家斯特凡纳·迪朗却不这么看,他从“蒙昧部落”获得灵感和启示:是时候换一种身份重新思考我们身处的世界了,不再以骄傲的人类视角,而是尝试用黑猩猩、抹香鲸、夜莺、昆虫、珊瑚礁、橡树乃至冰川或者山峦的“眼睛”去审视生态、反观人类,探索万物共生共荣的自然之道。基于这样的思考,他着手策划了“走向旷野”丛书,邀请来自科学、哲学、人文、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作者撰写“自然与人”的故事,以独到的人文生态主义视角和全新的叙事,代替沉默无言的大自然发声。就像他们的前辈法布尔(《昆虫记》作者)一样,这批法国作者向生活在沉闷单调钢筋水泥都市丛林中的读者们,展示了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在比利牛斯山脉的茂密森林里“与树同在”,在深不可测的海洋中见证抹香鲸惊人的智慧和复杂的社会结构,从普罗旺斯军营边的荒原狼到吉尔吉斯斯坦高山上的雪豹;从黄石国家公园的大灰熊到巴黎闹市厨房里的小蚯蚓,像一位“自然的侦探”那样追踪非凡生灵的足迹……在其中,生物多样性专家丽莎·加尔尼埃的作品《到自然中去!》显得别具一格,作者将两门看似毫无共同之处的科学——正向心理学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学结合起来,通过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回顾、统计数据分析和丰富多样的实践活动展示,陈述着这样一个久已为现代人忽略的常识:人类与自然是无法分割的整体,重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意味着对日渐脆弱的生态系统意义重大,同样关乎人类幸福感的获得和长久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
与记录某项具体的生态保护或自然探索的著作不同,《到自然中去!》可以看成一部自然与人的心理学研究综述,作者加尔尼埃阅读了至少上千份文献(感谢中译本出版社保留了这份超过全书1/4篇幅的资料目录),尝试着打通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心理科学和以自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生态科学之间的界限,从人类与自然的情感关联中揭示幸福感的核心来源。其中的许多研究,常令人有脑洞大开的惊喜。比如,心理学家苏珊·克莱顿提醒我们,参观动物园,或者与家里的宠物玩耍,尤其是与动物眼睛对视的那一刻,往往能获得一种跨越物种边界,独特而深沉的心理体验,“在这样的微妙时刻,两个生命通过大脑活动和生理反应感受到相同的东西,甚至融为一体。”比如,2017年一份对狗主人健康状况的研究报告显示,养狗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往往更低,并且宠物狗也常常成为打破隔离促进社交的媒介,就像我们常常在街头公园里看到的那样,狗狗们在打闹嬉戏,主人们在聊天。再比如,美国科学家的好几项研究表明,树木的一种“天然的镇静剂”,有效舒缓人们的精神疲劳——英国心理学家泰勒甚至宣称,“居住地附近树木越少,伦敦人柜子里抗抑郁的药品就越多”!
加尔尼埃强调,重新建立与自然的良性互动还有着更加深远的人文价值。正如不少历史学家揭示的那样,尽管今天的人类世界依旧充满各种争端,但我们无疑在朝着合作的大方向前进。至于未来的命运如何,取决于多重要素的共同作用,其中之一就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也就是同情心、自制力、道德感和理性。而处理好与“非人类”生态世界的关系,正是帮助人们找到这个内心“天使”的重要途径。
800年前,中国词人辛弃疾说,“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800年后,法国学人呼吁我们“到自然中去!坐在草坪上,在树荫下,在小溪旁;轻柔地抚摸小猫或者小狗,观察身边的花草,聆听鸟鸣,在雨幕中深呼吸;奔跑、爬行、悠闲地漫步、慵懒地休憩;与朋友见面、交谈、拥抱、大笑,爱人或者被爱……”实际上都在表达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人类仍希望拥有美好的未来,就一定要学会与其他生物相互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