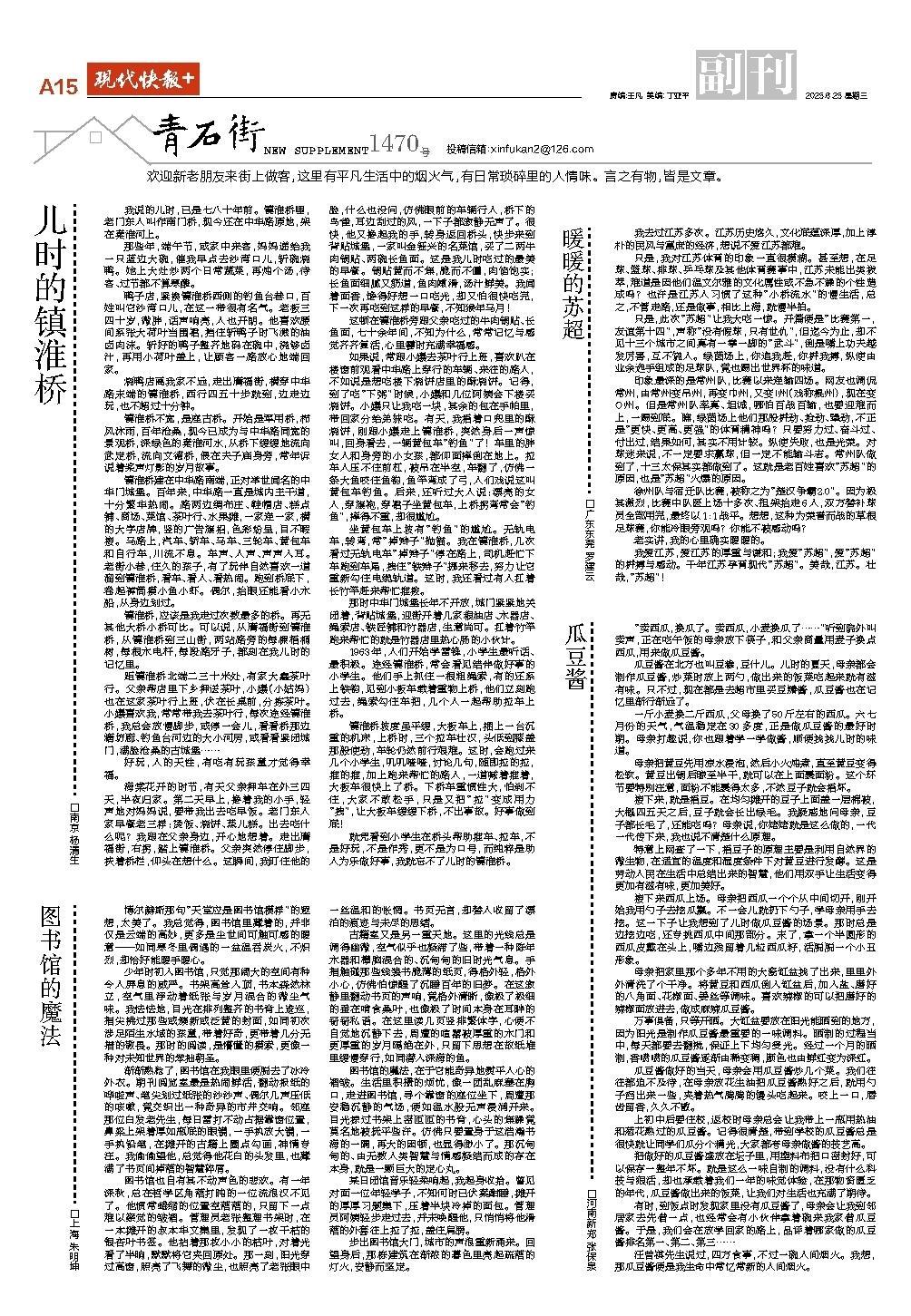□河南新郑 张保泉
“卖西瓜,换瓜了。卖西瓜,小麦换瓜了……”听到院外叫卖声,正在吃午饭的母亲放下筷子,和父亲商量用麦子换点西瓜,用来做瓜豆酱。
瓜豆酱在北方也叫豆糁,豆什儿。儿时的夏天,母亲都会制作瓜豆酱,炒菜时放上两勺,做出来的饭菜吃起来就有滋有味。只不过,现在都是去超市里买豆瓣酱,瓜豆酱也在记忆里渐行渐远了。
一斤小麦换二斤西瓜,父母换了50斤左右的西瓜。六七月份的天气,气温稳定在30多度,正是做瓜豆酱的最好时期。母亲打趣说,你也跟着学一学做酱,顺便找找儿时的味道。
母亲把黄豆先用凉水浸泡,然后小火炖煮,直至黄豆变得松软。黄豆出锅后晾至半干,就可以在上面裹面粉。这个环节要特别注意,面粉不能裹得太多,不然豆子就会捂坏。
接下来,就是捂豆。在均匀摊开的豆子上面盖一层棉被,大概四五天之后,豆子就会长出绿毛。我疑惑地问母亲,豆子都长毛了,还能吃吗?母亲说,你姥姥就是这么做的,一代一代传下来,我也说不清楚什么原理。
特意上网查了一下,捂豆子的原理主要是利用自然界的微生物,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对黄豆进行发酵。这是劳动人民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智慧,他们用双手让生活变得更加有滋有味,更加美好。
接下来西瓜上场。母亲把西瓜一个个从中间切开,刚开始我用勺子去挖瓜瓤。不一会儿就扔下勺子,学母亲用手去挖。这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儿时做瓜豆酱的场景。那时总是边挖边吃,还专挑西瓜中间那部分。末了,拿一个半圆形的西瓜皮戴在头上,嘴边残留着几粒西瓜籽,活脱脱一个小丑形象。
母亲把家里那个多年不用的大瓷缸盆找了出来,里里外外清洗了个干净。将黄豆和西瓜倒入缸盆后,加入盐、磨好的八角面、花椒面、姜丝等调味。喜欢辣椒的可以把磨好的辣椒面放进去,做成麻辣瓜豆酱。
万事俱备,只等开晒。大缸盆要放在阳光能晒到的地方,因为阳光是制作瓜豆酱最重要的一味调料。晒制的过程当中,每天都要去翻搅,保证上下均匀受光。经过一个月的晒制,香喷喷的瓜豆酱逐渐由稀变稠,颜色也由鲜红变为深红。
瓜豆酱做好的当天,母亲会用瓜豆酱炒几个菜。我们往往都迫不及待,在母亲放花生油把瓜豆酱熟好之后,就用勺子舀出来一些,夹着热气腾腾的馒头吃起来。咬上一口,唇齿留香,久久不散。
上初中后要住校,返校时母亲总会让我带上一瓶用热油和葱花熟过的瓜豆酱。记得很清楚,带到学校的瓜豆酱总是很快就让同学们瓜分个精光,大家都夸母亲做酱的技艺高。
把做好的瓜豆酱盛放在坛子里,用塑料布把口密封好,可以保存一整年不坏。就是这么一味自制的调料,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却也承载着我们一年的味觉体验,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瓜豆酱做出来的饭菜,让我们对生活也充满了期待。
有时,到饭点时发现家里没有瓜豆酱了,母亲会让我到邻居家去先借一点,也经常会有小伙伴拿着碗来我家借瓜豆酱。于是,我们会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品评着哪家做的瓜豆酱排名第一、第二、第三……
汪曾祺先生说过,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想,那瓜豆酱便是我生命中常忆常新的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