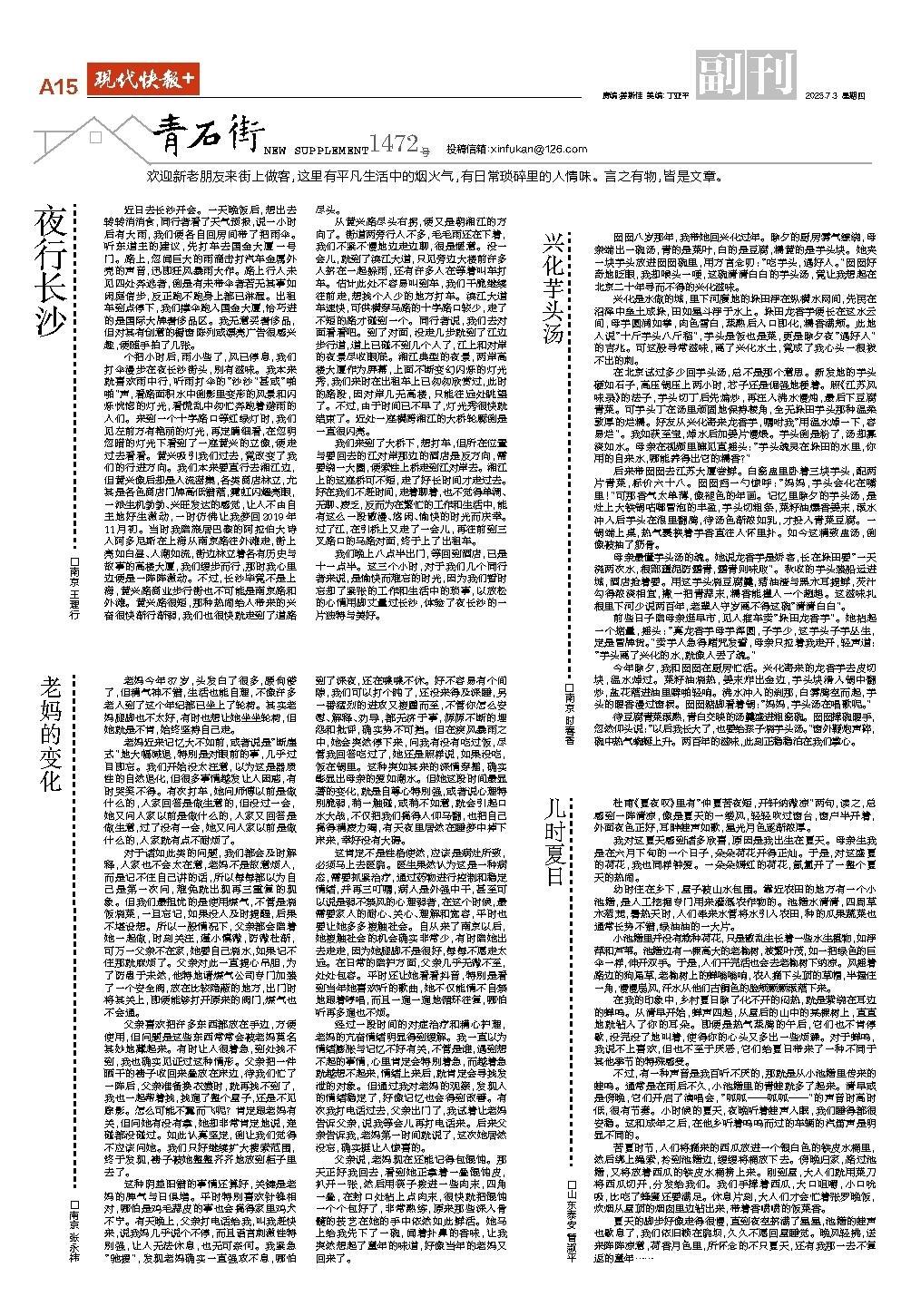□南京 时春香
囡囡八岁那年,我带她回兴化过年。除夕的厨房雾气缭绕,母亲端出一碗汤,青的是菜叶,白的是豆腐,糯黄的是芋头块。她夹一块芋头放进囡囡碗里,用方言念叨:“吃芋头,遇好人。”囡囡好奇地眨眼,我却喉头一哽,这碗清清白白的芋头汤,竟让我想起在北京二十年寻而不得的兴化滋味。
兴化是水做的城,里下河腹地的垛田浮在纵横水网间,先民在沼泽中垒土成垛,田如星斗浮于水上。垛田龙香芋便长在这水云间,母芋圆润如拳,肉色雪白,蒸熟后入口即化,糯香满颊。此地人说“十斤芋头八斤稻”,芋头是饭也是菜,更是除夕夜“遇好人”的吉兆。可这般寻常滋味,离了兴化水土,竟成了我心头一根拔不出的刺。
在北京试过多少回芋头汤,总不是那个意思。新发地的芋头硬如石子,高压锅压上两小时,芯子还是倔强地梗着。照《江苏风味录》的法子,芋头切丁后先煸炒,再注入沸水慢炖,最后下豆腐青菜。可芋头丁在汤里顽固地保持棱角,全无垛田芋头那种温柔敦厚的烂糯。好友从兴化寄来龙香芋,嘱咐我“用温水焯一下,容易烂”。我如获至宝,焯水后加姜片慢煨。芋头倒是粉了,汤却寡淡如水。母亲在视频里瞧见直摇头:“芋头魂灵在垛田的水里,你用的自来水,哪能养得出它的糯香?”
后来带囡囡去江苏大厦尝鲜。白瓷盅里卧着三块芋头,配两片青菜,标价六十八。囡囡舀一勺惊呼:“妈妈,芋头会化在嘴里!”可那香气太单薄,像褪色的年画。记忆里除夕的芋头汤,是灶上大铁锅咕嘟冒泡的丰盈,芋头切粗条,菜籽油爆香姜末,滚水冲入后芋头在浪里翻腾,待汤色渐浓如乳,才投入青菜豆腐。一锅端上桌,热气裹挟着芋香直往人怀里扑。如今这精致盅汤,倒像被抽了筋骨。
母亲最懂芋头汤的魂。她说龙香芋是娇客,长在垛田要“一天浇两次水,根部壅泥防露青,露青则味败”。秋收的芋头装船运进城,酒店抢着要。用这芋头烧豆腐羹,猪油渣与黑木耳提鲜,芡汁勾得浓淡相宜,撒一把青蒜末,糯香能撞人一个趔趄。这滋味扎根里下河少说两百年,老辈人守岁离不得这碗“清清白白”。
前些日子陪母亲逛早市,见人推车卖“垛田龙香芋”。她拈起一个掂量,摇头:“真龙香芋母芋浑圆,子芋少,这芋头子芋丛生,定是冒牌货。”卖芋人急得赌咒发誓,母亲只拉着我走开,轻声道:“芋头离了兴化的水,就像人丢了魂。”
今年除夕,我和囡囡在厨房忙活。兴化寄来的龙香芋去皮切块,温水焯过。菜籽油烧热,姜末炸出金边,芋头块滑入锅中翻炒,盐花落进油里噼啪轻响。沸水冲入的刹那,白雾腾空而起,芋头的暖香漫过窗棂。囡囡踮脚看着锅:“妈妈,芋头汤在唱歌呢。”
待豆腐青菜滚熟,青白交映的汤羹盛进粗瓷碗。囡囡捧碗暖手,忽然仰头说:“以后我长大了,也要给孩子烧芋头汤。”窗外鞭炮声碎,碗中热气蜿蜒上升。两百年的滋味,此刻正稳稳泊在我们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