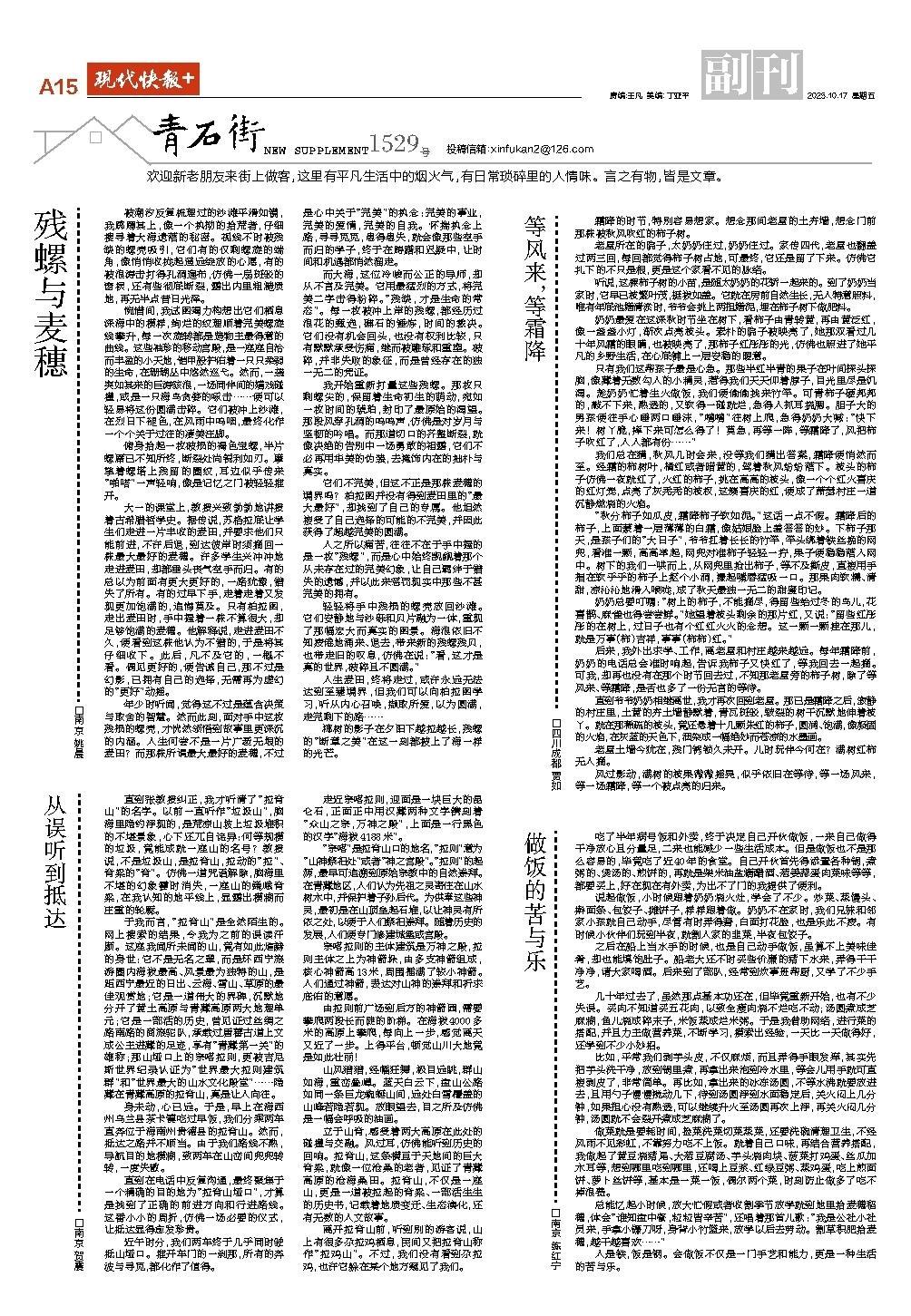□南京 姚晨
被潮汐反复梳理过的沙滩平滑如镜,我踯躅其上,像一个执拗的拾荒者,仔细搜寻着大海遗落的秘密。视线不时被残缺的螺壳吸引,它们有的仅剩螺旋的端角,像悄悄收拢起遥远绽放的心愿,有的被浪涛击打得孔洞遍布,仿佛一扇斑驳的窗棂,还有些彻底断裂,露出内里粗糙质地,再无半点昔日光泽。
惋惜间,我试图竭力构想出它们栖息深海中的模样,绚烂的纹理顺着完美螺旋线攀升,每一次旋转都是造物主最得意的曲线。这些袖珍的移动宫殿,是一座座自洽而丰盈的小天地,铠甲般护佑着一只只柔弱的生命,在珊瑚丛中悠然巡弋。然而,一袭突如其来的巨涛骇浪,一场同伴间的嬉戏碰撞,或是一只海鸟贪婪的啄击……便可以轻易将这份圆满击碎。它们被冲上沙滩,在烈日下褪色,在风雨中呜咽,最终化作一个个关于过往的凄美注脚。
俯身拾起一枚破损的褐色宝螺,半片螺厣已不知所终,断裂处尚锐利如刃。摩挲着螺塔上残留的圈纹,耳边似乎传来“啪嗒”一声轻响,像是记忆之门被轻轻推开。
大一的课堂上,教授兴致勃勃地讲授着古希腊哲学史。据传说,苏格拉底让学生们走进一片丰收的麦田,并要求他们只能前进,不许后退,到达彼岸时须摘回一株最大最好的麦穗。许多学生兴冲冲地走进麦田,却都垂头丧气空手而归。有的总以为前面有更大更好的,一路犹豫,错失了所有。有的过早下手,走着走着又发现更加饱满的,追悔莫及。只有柏拉图,走出麦田时,手中握着一株不算很大,却足够饱满的麦穗。他解释说,走进麦田不久,便看到这株他认为不错的,于是将其仔细收下。此后,凡不及它的,一概不看。偶见更好的,便告诫自己,那不过是幻影,已拥有自己的选择,无需再为虚幻的“更好”动摇。
年少时听闻,觉得这不过是蕴含决策与取舍的智慧。然而此刻,面对手中这枚残损的螺壳,才恍然领悟到故事里更深沉的内涵。人生何尝不是一片广袤无垠的麦田?而那株所谓最大最好的麦穗,不过是心中关于“完美”的执念:完美的事业,完美的爱情,完美的自我。怀揣执念上路,寻寻觅觅,患得患失,就会像那些空手而归的学子,终于在踌躇和迟疑中,让时间和机遇都悄然溜走。
而大海,这位冷峻而公正的导师,却从不言及完美。它用最猛烈的方式,将完美二字击得粉碎。“残缺,才是生命的常态”。每一枚被冲上岸的残螺,都经历过浪花的甄选,礁石的锤炼,时间的裁决。它们没有机会回头,也没有权利比较,只有默默承受伤痛,继而被雕琢和重塑。破碎,并非失败的象征,而是曾经存在的独一无二的凭证。
我开始重新打量这些残螺。那枚只剩螺尖的,保留着生命初生的萌动,宛如一枚时间的琥珀,封印了最原始的渴望。那段风穿孔洞的呜鸣声,仿佛是对岁月与坚韧的吟唱。而那道切口的齐整断裂,就像决绝的告别中一场勇敢的袒露,它们不必再用华美的伪装,去掩饰内在的拙朴与真实。
它们不完美,但这不正是那株麦穗的境界吗?柏拉图并没有得到麦田里的“最大最好”,却找到了自己的专属。他坦然接受了自己选择的可能的不完美,并因此获得了超越完美的圆满。
人之所以痛苦,往往不在于手中握的是一枚“残螺”,而是心中始终觊觎着那个从未存在过的完美幻象,让自己羁绊于错失的遗憾,并以此来惩罚现实中那些不甚完美的拥有。
轻轻将手中残损的螺壳放回沙滩。它们安静地与沙砾和贝片融为一体,重现了那幅宏大而真实的图景。海浪依旧不知疲倦地涌来、退去,带来新的残螺残贝,也带走旧的叹息,仿佛在说:“看,这才是真的世界,破碎且不圆满。”
人生麦田,终将走过,或许永远无法达到至臻境界,但我们可以向柏拉图学习,听从内心召唤,撷取所爱,以为圆满,走完剩下的路……
椰树的影子在夕阳下越拉越长,残螺的“断章之美”在这一刻都披上了海一样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