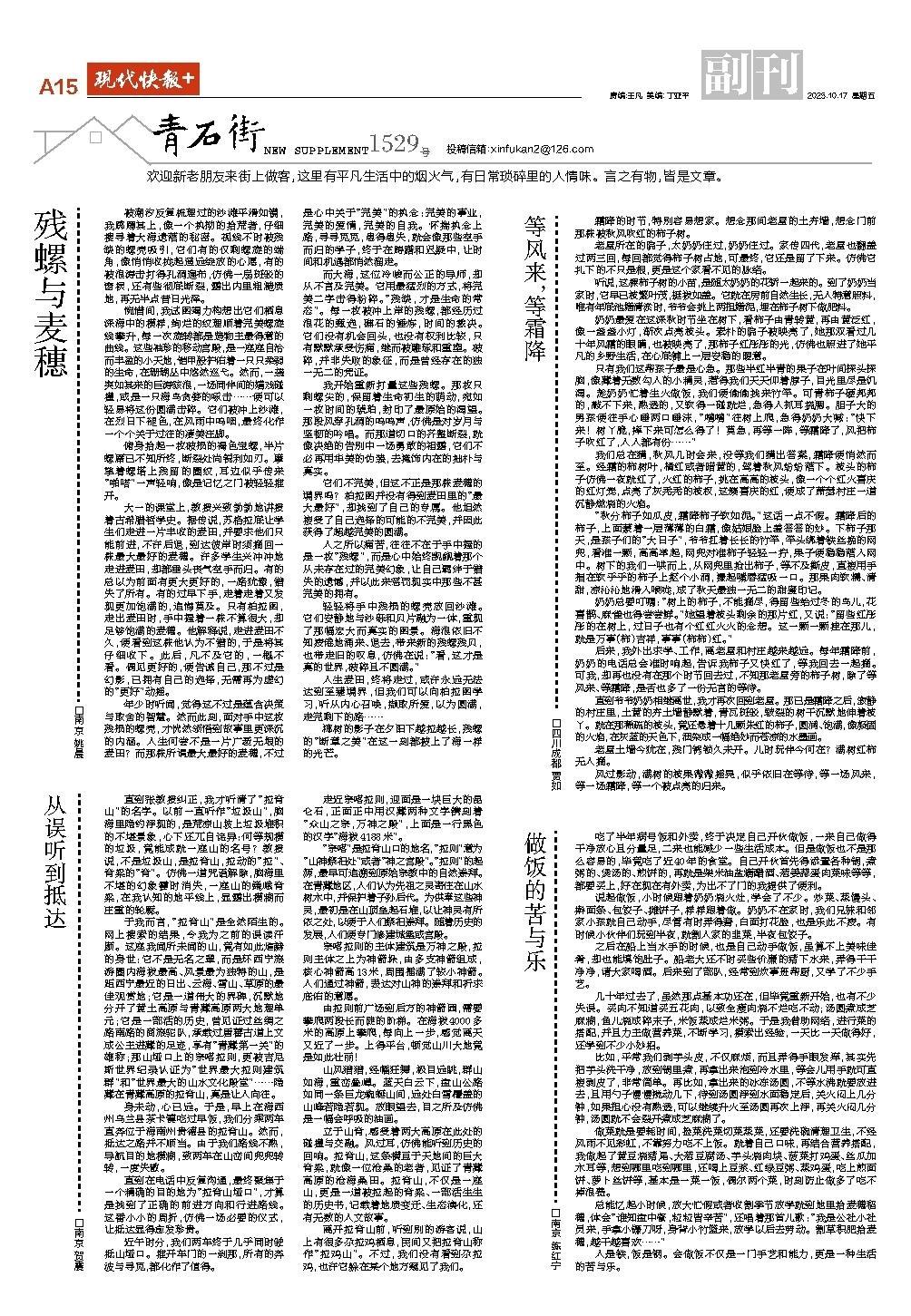□四川成都 贾如
霜降的时节,特别容易想家。想念那间老屋的土夯墙,想念门前那株被秋风吹红的柿子树。
老屋所在的院子,太奶奶住过,奶奶住过。家传四代,老屋也翻盖过两三回,每回都觉得柿子树占地,可最终,它还是留了下来。仿佛它扎下的不只是根,更是这个家看不见的脉络。
听说,这棵柿子树的小苗,是随太奶奶的花轿一起来的。到了奶奶当家时,它早已枝繁叶茂,挺拔如盖。它就在房前自然生长,无人特意照料,唯有年底池塘清淤时,爷爷会挑上两担塘泥,埋在柿子树下做肥料。
奶奶最爱在这深秋时节坐在树下,看柿子由青转黄,再由黄泛红,像一盏盏小灯,渐次点亮枝头。素朴的院子被映亮了,她那双看过几十年风霜的眼睛,也被映亮了,那柿子红彤彤的光,仿佛也照进了她平凡的乡野生活,在心底铺上一层安稳的暖意。
只有我们这帮孩子最是心急。那些半红半青的果子在叶间探头探脑,像藏着无数勾人的小精灵,惹得我们天天仰着脖子,目光里尽是饥渴。趁奶奶忙着生火做饭,我们便偷偷找来竹竿。可青柿子硬邦邦的,敲不下来,熟透的,又软得一碰就烂,急得人抓耳挠腮。胆子大的男孩便往手心唾两口唾沫,“噌噌”往树上爬,急得奶奶大喊:“快下来!树丫脆,摔下来可怎么得了!莫急,再等一阵,等霜降了,风把柿子吹红了,人人都有份……”
我们总在猜,秋风几时会来,没等我们猜出答案,霜降便悄然而至。经霜的柿树叶,橘红或者暗黄的,驾着秋风纷纷落下。枝头的柿子仿佛一夜就红了,火红的柿子,挑在高高的枝头,像一个个红火喜庆的红灯笼,点亮了灰秃秃的枝杈,这簇喜庆的红,便成了萧瑟村庄一道沉静燃烧的火焰。
“秋分柿子如瓜皮,霜降柿子软如泥。”这话一点不假。霜降后的柿子,上面蒙着一层薄薄的白霜,像姑娘脸上羞答答的纱。下柿子那天,是孩子们的“大日子”,爷爷扛着长长的竹竿,竿头绑着铁丝挽的网兜,看准一颗,高高举起,网兜对准柿子轻轻一拧,果子便稳稳落入网中。树下的我们一哄而上,从网兜里抢出柿子,等不及撕皮,直接用手指在软乎乎的柿子上抠个小洞,撮起嘴唇猛吸一口。那果肉软糯、清甜,凉沁沁地滑入喉咙,成了秋天最独一无二的甜蜜印记。
奶奶总要叮嘱:“树上的柿子,不能摘尽,得留些给过冬的鸟儿,花喜鹊、麻雀也得尝尝鲜。”她望着枝头剩余的那片红,又说:“留些红彤彤的在树上,过日子也有个红红火火的念想。这一颗一颗挂在那儿,就是万事(柿)吉祥,事事(柿柿)红。”
后来,我外出求学、工作,离老屋和村庄越来越远。每年霜降前,奶奶的电话总会准时响起,告诉我柿子又快红了,等我回去一起摘。可我,却再也没有在那个时节回去过,不知那老屋旁的柿子树,除了等风来、等霜降,是否也多了一份无言的等待。
直到爷爷奶奶相继离世,我才再次回到老屋。那已是霜降之后,寂静的村庄里,土黄的夯土墙静默着,青瓦斑驳,皲裂的树干沉默地伸着枝丫。就在那稀疏的枝头,竟还悬着十几颗朱红的柿子,圆润、饱满,像凝固的火焰,在灰蓝的天色下,洇染成一幅绝妙而苍凉的水墨画。
老屋土墙今犹在,残门锈锁久未开。儿时玩伴今何在?满树红柿无人摘。
风过影动,满树的枝果微微摇晃,似乎依旧在等待,等一场风来,等一场霜降,等一个被点亮的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