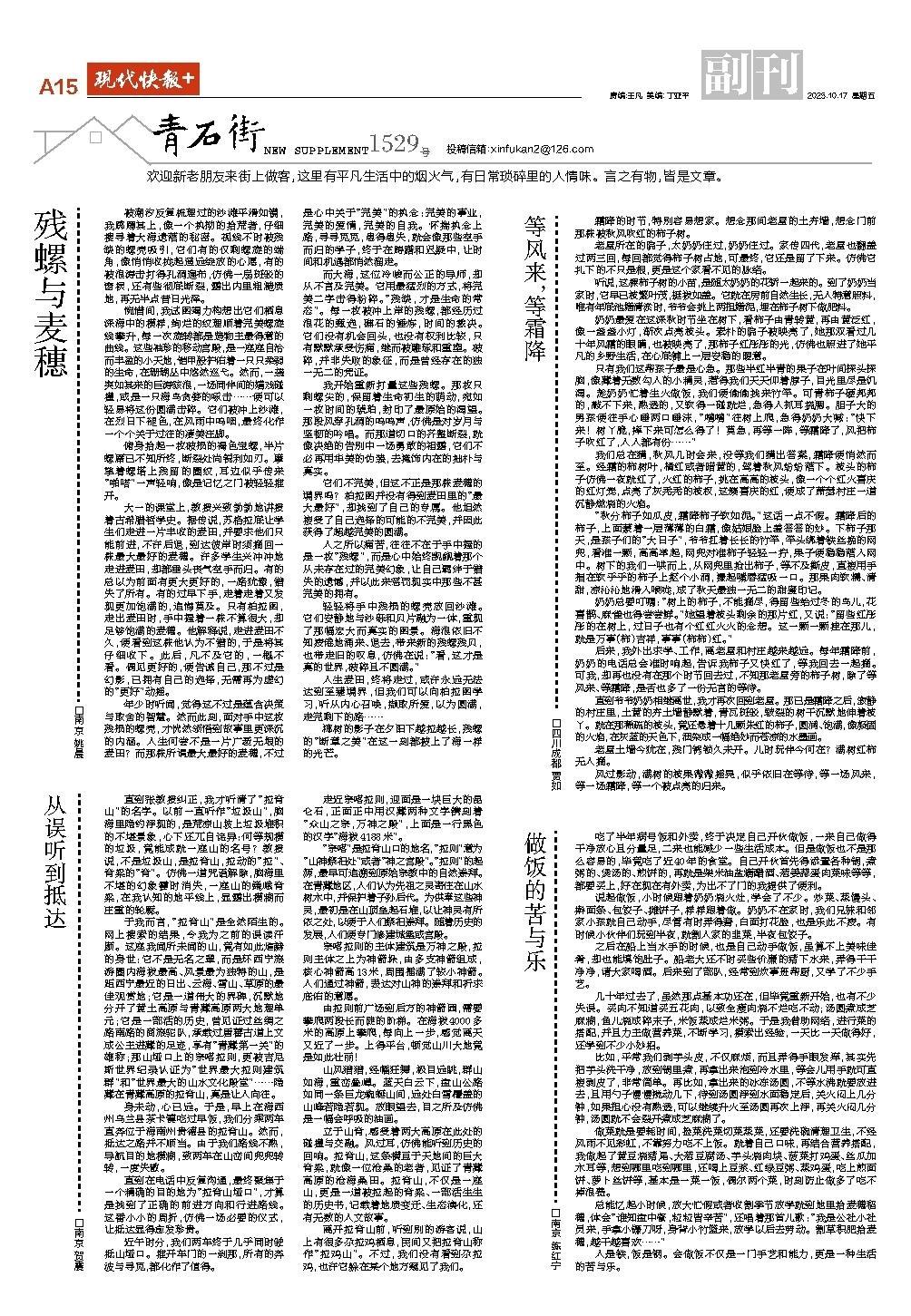□南京 贺震
直到张教授纠正,我才听清了“拉脊山”的名字。以前一直听作“垃圾山”,脑海里隐约浮现的,是荒凉山坡上垃圾堆积的不堪景象,心下还兀自诧异:何等规模的垃圾,竟能成就一座山的名号?教授说,不是垃圾山,是拉脊山,拉动的“拉”、脊梁的“脊”。仿佛一道咒语解除,脑海里不堪的幻象霎时消失,一座山的巍峨脊梁,在我认知的地平线上,显露出模糊而庄重的轮廓。
于我而言,“拉脊山”是全然陌生的。网上搜索的结果,令我为之前的误读汗颜。这座我闻所未闻的山,竟有如此煊赫的身世:它不是无名之辈,而是环西宁旅游圈内海拔最高、风景最为独特的山,是距西宁最近的日出、云海、雪山、草原的最佳观赏地;它是一道伟大的界碑,沉默地分开了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两大地理单元;它是一部活的历史,曾见证过丝绸之路南路的商旅驼队,承载过唐蕃古道上文成公主进藏的足迹,享有“青藏第一关”的雄称;那山垭口上的宗喀拉则,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为“世界最大拉则建筑群”和“世界最大的山水文化殿堂”……隐藏在青藏高原的拉脊山,真是让人向往。
身未动,心已远。于是,早上在海西州乌兰县茶卡镇吃过早饭,我们分乘两车直奔位于海南州贵德县的拉脊山。然而,抵达之路并不顺当。由于我们路线不熟,导航目的地模糊,致两车在山峦间兜兜转转,一度失散。
直到在电话中反复沟通,最终聚焦于一个精确的目的地为“拉脊山垭口”,才算是找到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和行进路线。这番小小的周折,仿佛一场必要的仪式,让抵达显得愈发珍贵。
近午时分,我们两车终于几乎同时驶抵山垭口。推开车门的一刹那,所有的奔波与寻觅,都化作了值得。
走近宗喀拉则,迎面是一块巨大的昆仑石,正面正中用汉藏两种文字镌刻着“众山之宗,万神之殿”,上面是一行黑色的汉字“海拔4188米”。
“宗喀”是拉脊山口的地名,“拉则”意为“山神祭祀处”或者“神之宫殿”。“拉则”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原始宗教中的自然崇拜。在青藏地区,人们认为先祖之灵寄住在山水树木中,并保护着子孙后代。为供奉这些神灵,最初是在山顶垒起石堆,以让神灵有所依之处,以便于人们祭祀崇拜。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便专门修建城堡或宫殿。
宗喀拉则的主体建筑是万神之殿,拉则主体之上为神箭垛,由多支神箭组成,核心神箭高13米,周围插满了较小神箭。人们通过神箭,表达对山神的崇拜和祈求庇佑的意愿。
由拉则前广场到后方的神箭园,需要攀爬两段长而陡的阶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攀爬,每向上一步,感觉离天又近了一步。上得平台,顿觉山川大地竟是如此壮丽!
山风猎猎,经幡狂舞,极目远眺,群山如海,重峦叠嶂。蓝天白云下,盘山公路如同一条巨龙蜿蜒山间,远处白雪覆盖的山峰若隐若现。放眼望去,目之所及仿佛是一幅会呼吸的油画。
立于山脊,感受着两大高原在此处的碰撞与交融。风过耳,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响。拉脊山,这条横亘于天地间的巨大脊梁,就像一位沧桑的老者,见证了青藏高原的沧海桑田。拉脊山,不仅是一座山,更是一道被拉起的脊梁、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书,记载着地质变迁、生态演化,还有无数的人文故事。
离开拉脊山前,听到别的游客说,山上有很多尕拉鸡栖息,民间又把拉脊山称作“拉鸡山”。不过,我们没有看到尕拉鸡,也许它躲在某个地方窥见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