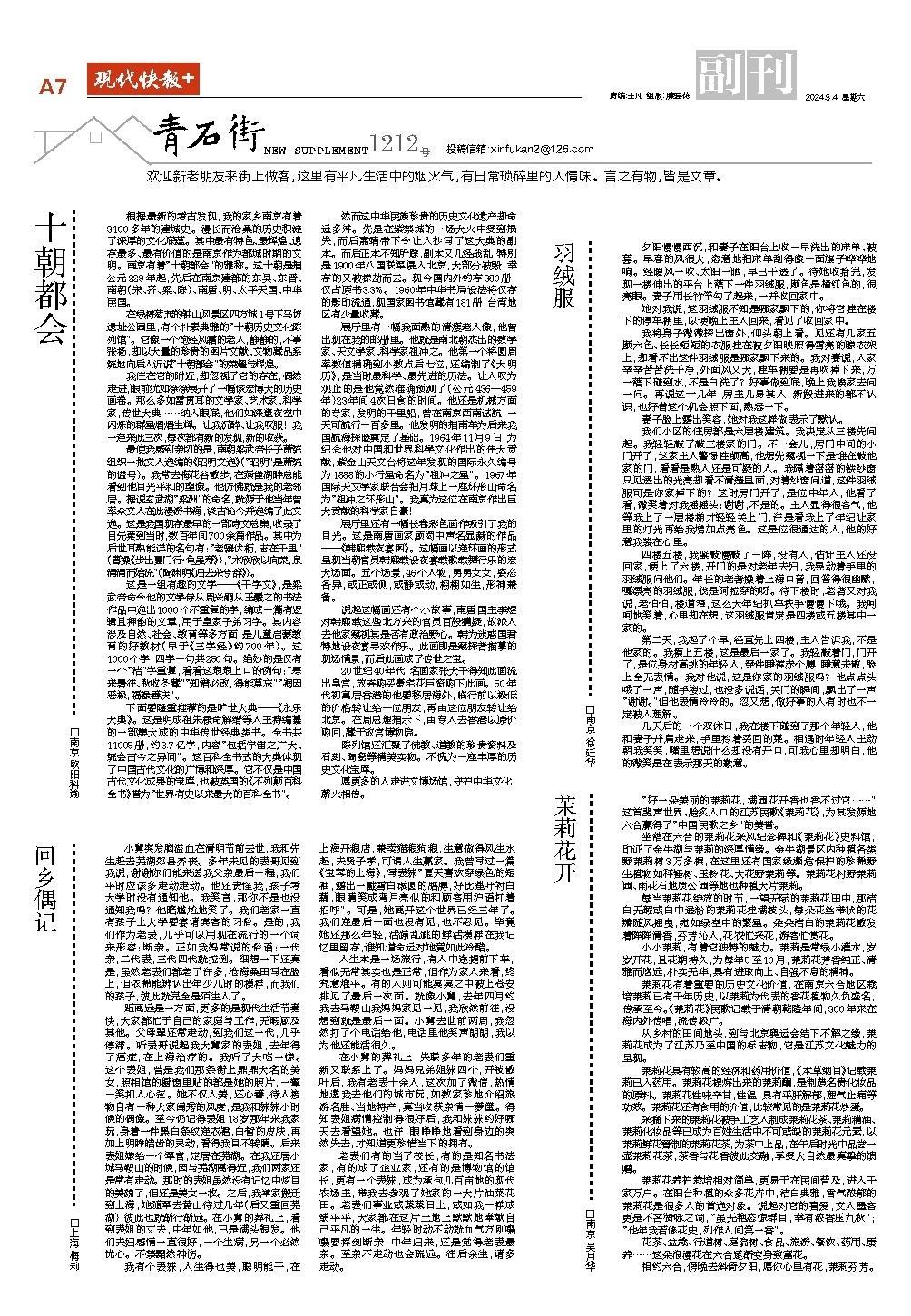□南京 徐廷华
夕阳慢慢西沉,和妻子在阳台上收一早洗出的床单、被套。早春的风很大,恣意地把床单刮得像一面旗子哗哗地响。经暖风一吹、太阳一晒,早已干透了。待她收拾完,发现一楼伸出的平台上落下一件羽绒服,颜色是橘红色的,很亮眼。妻子用长竹竿勾了起来,一并收回家中。
她对我说,这羽绒服不知是哪家飘下的,你将它挂在楼下的停车棚里,以便晚上主人回来,看见了收回家中。
我将身子微微探出窗外,仰头朝上看。见还有几家五颜六色、长长短短的衣服挂在被夕阳映照得雪亮的晾衣架上,却看不出这件羽绒服是哪家飘下来的。我对妻说,人家辛辛苦苦洗干净,外面风又大,挂车棚要是再吹掉下来,万一落下碰到水,不是白洗了?好事做到底,晚上我挨家去问一问。再说这十几年,房主几易其人,新搬进来的都不认识,也好借这个机会照下面,熟悉一下。
妻子脸上露出笑容,她对我这样做表示了默认。
我们小区的住房都是六层楼建筑。我决定从三楼先问起。我轻轻敲了敲三楼家的门。不一会儿,房门中间的小门开了,这家主人警惕性颇高,他想先窥视一下是谁在敲他家的门,看看是熟人还是可疑的人。我隔着密密的铁纱窗只见透出的光亮却看不清楚里面,对着纱窗问道,这件羽绒服可是你家掉下的?这时房门开了,是位中年人,他看了看,微笑着对我摇摇头:谢谢,不是的。主人显得很客气,他等我上了一层楼梯才轻轻关上门,许是看我上了年纪让家里的灯光再给我增加点亮色。这是位很通达的人,他的好意我装在心里。
四楼五楼,我紧敲慢敲了一阵,没有人,估计主人还没回家,便上了六楼,开门的是对老年夫妇,我晃动着手里的羽绒服问他们。年长的老者操着上海口音,回答得很幽默,嘎漂亮的羽绒服,伐是阿拉穿的呀。待下楼时,老者又对我说,老伯伯,楼道窄,这么大年纪抓牢扶手慢慢下哦。我呵呵地笑着,心里却在想,这羽绒服肯定是四楼或五楼其中一家的。
第二天,我起了个早,径直先上四楼,主人告诉我,不是他家的。我摸上五楼,这是最后一家了。我轻敲着门,门开了,是位身材高挑的年轻人,穿件睡裤赤个膊,睡意未散,脸上全无表情。我对他说,这是你家的羽绒服吗?他点点头哦了一声,随手接过,也没多说话,关门的瞬间,飘出了一声“谢谢。”但他表情冷冷的。忽又想,做好事的人有时也不一定被人理解。
几天后的一个双休日,我在楼下碰到了那个年轻人,他和妻子并肩走来,手里拎着买回的菜。相遇时年轻人主动朝我笑笑,嘴里想说什么却没有开口,可我心里却明白,他的微笑是在表示那天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