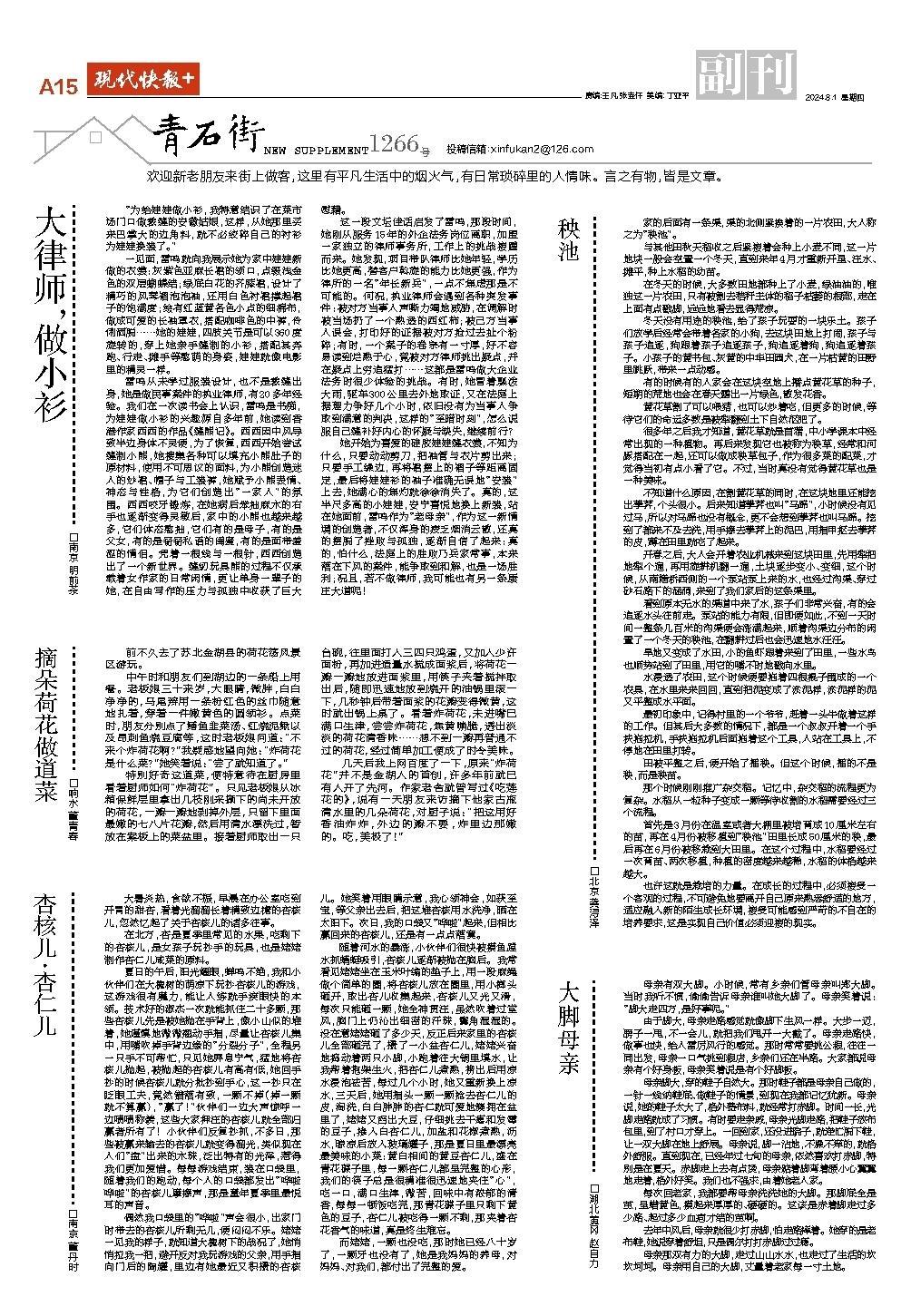□北京 龚浔泽
家的后面有一条渠,渠的北侧紧挨着的一片农田,大人称之为“秧池”。
与其他田秋天稻收之后紧接着会种上小麦不同,这一片地块一般会空置一个冬天,直到来年4月才重新开垦、注水、摊平,种上水稻的幼苗。
在冬天的时候,大多数田地都种上了小麦,绿油油的,唯独这一片农田,只有被割去秸秆主体的稻子枯萎的根部,走在上面有点戳脚,远远地看去显得荒凉。
冬天没有用途的秧池,给了孩子玩耍的一块乐土。孩子们放学后经常会带着各家的小狗,去这块田地上打闹,孩子与孩子追逐,狗跟着孩子追逐孩子,狗追逐着狗,狗追逐着孩子。小孩子的黄书包、灰黄的中华田园犬,在一片枯黄的田野里跳跃,带来一点动感。
有的时候有的人家会在这块空地上播点黄花草的种子,短期的荒地也会在春天露出一片绿色,散发花香。
黄花草割了可以喂猪,也可以炒着吃,但更多的时候,等待它们的命运多数是被犁翻到土下自然沤肥了。
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黄花草就是苜蓿,中小学课本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植物。再后来发现它也被称为秧草,经常和河豚搭配在一起,还可以做成秧草包子,作为很多菜的配菜,才觉得当初有点小看了它。不过,当时真没有觉得黄花草也是一种美味。
不知道什么原因,在割黄花草的同时,在这块地里还能挖出荸荠,个头很小。后来知道荸荠也叫“马蹄”,小时候没有见过马,所以对马蹄也没有概念,更不会想到荸荠也叫马蹄。挖到了都来不及去洗,用手擦去荸荠上的泥巴,用指甲抠去荸荠的皮,蹲在田里就吃了起来。
开春之后,大人会开着农业机械来到这块田里,先用犁把地犁个遍,再用旋耕机翻一遍,土块逐步变小、变细,这个时候,从南塘桥西侧的一个泵站泵上来的水,也经过沟渠、穿过砂石路下的涵洞,来到了我们家后的这条渠里。
看到原本无水的渠道中来了水,孩子们非常兴奋,有的会追逐水头往前走。泵站的能力有限,但即便如此,不到一天时间一整条几百米的沟渠便会涨满起来,顺着沟渠边分布的闲置了一个冬天的秧池,在翻耕过后也会迅速地水汪汪。
旱地又变成了水田,小的鱼虾跟着来到了田里,一些水鸟也顺势站到了田里,用它的嘴不时地戳向水里。
水浸透了农田,这个时候便要拖着四根棍子围成的一个农具,在水里来来回回,直到把泥变成了淤泥样,淤泥样的泥又平整成水平面。
最初印象中,记得村里的一个爷爷,赶着一头牛做着这样的工作。但其后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一个叔叔开着一个手扶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后面拖着这个工具,人站在工具上,不停地在田里打转。
田被平整之后,便开始了插秧。但这个时候,插的不是秧,而是秧苗。
那个时候刚刚推广杂交稻。记忆中,杂交稻的流程更为复杂。水稻从一粒种子变成一颗等待收割的水稻需要经过三个流程。
首先是3月份在温室或者大棚里被培育成10厘米左右的苗,再在4月份被移植到“秧池”田里长成50厘米的秧,最后再在6月份被移栽到大田里。在这个过程中,水稻要经过一次育苗、两次移植,种植的密度越来越稀,水稻的体格越来越大。
也许这就是栽培的力量。在成长的过程中,必须接受一个客观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离开自己原来熟悉舒适的地方,适应融入新的陌生成长环境,接受可能感到严苛的不自在的培养要求,这是实现自己价值必须迎接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