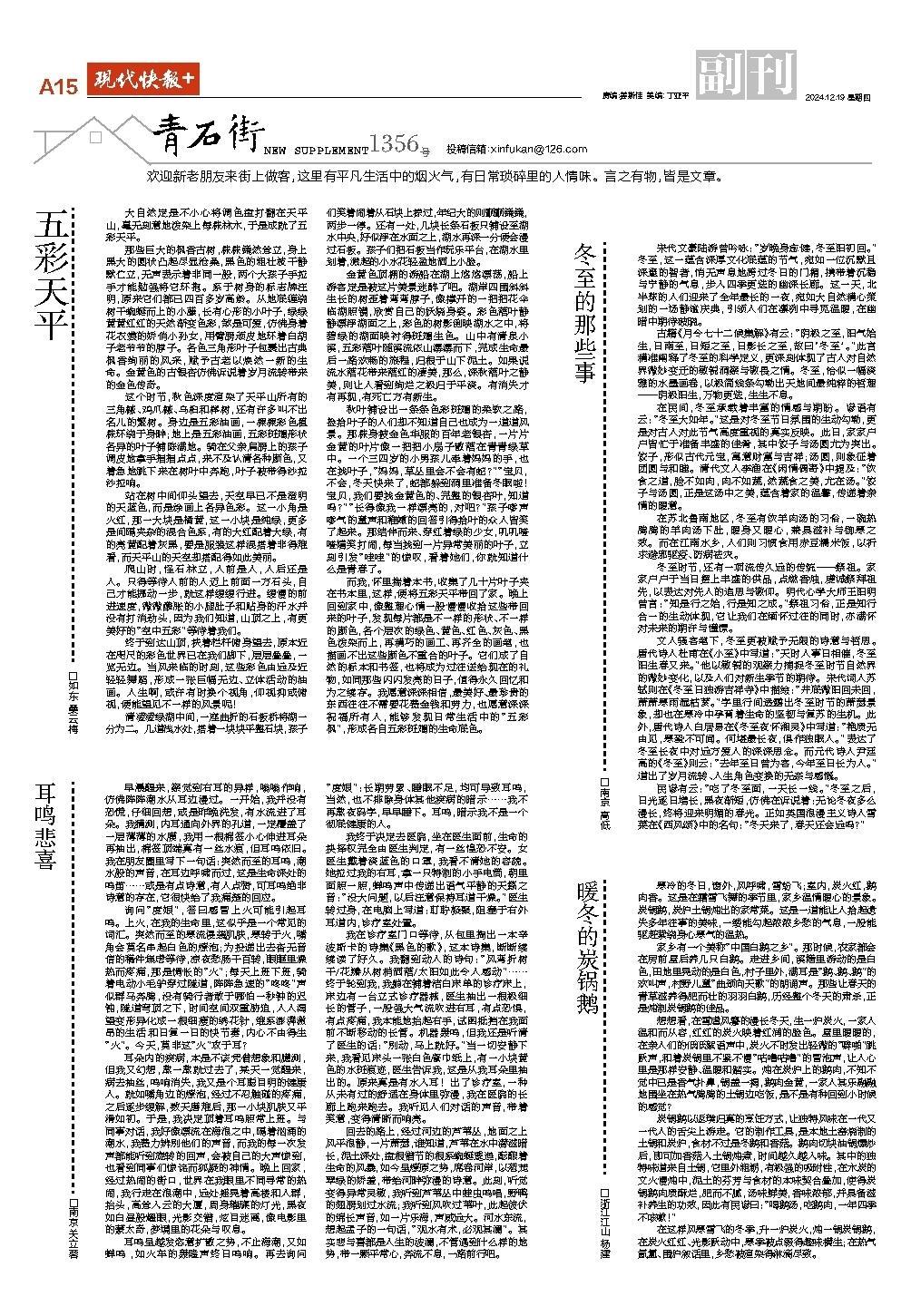□南京 关立蓉
早晨醒来,察觉到右耳的异样,嗡嗡作响,仿佛阵阵潮水从耳边漫过。一开始,我并没有恐慌,仔细回想,或是昨晚洗发,有水流进了耳朵。我猜测,内耳通向外界的孔道,一定覆盖了一层薄薄的水膜,我用一根棉签小心伸进耳朵再抽出,棉签顶端真有一丝水痕,但耳鸣依旧。我在朋友圈里写下一句话:突然而至的耳鸣,潮水般的声音,在耳边呼啸而过,这是生命深处的鸣笛……或是有点诗意,有人点赞,可耳鸣绝非诗意的存在,它很快给了我痛楚的回应。
询问“度娘”,答曰感冒上火可能引起耳鸣。上火,在我的生命里,这似乎是一个常见的词汇。突然而至的寒流侵袭肌肤,寒转于火,嘴角会莫名串起白色的燎泡;为投递出去杳无音信的稿件焦虑等待,凉夜愁肠千百转,眼眶里燥热而疼痛,那是惆怅的“火”;每天上班下班,骑着电动小毛驴穿过隧道,阵阵急速的“咚咚”声似群马奔腾,没有骑行者敢于哪怕一秒钟的迟钝,隧道穹顶之下,时间空间双重胁迫,人人渴望变形异化成一根细瘦的绣花针,维系澎湃激昂的生活 和日复一日的快节奏,内心不由得生“火”。今天,莫非这“火”攻于耳?
耳朵内的疾病,本是不该凭借想象和臆测,但我又幻想,熬一熬就过去了,某天一觉醒来,病去抽丝,鸣响消失,我又是个耳聪目明的健康人。就如嘴角边的燎泡,经过不忍触碰的疼痛,之后逐步缓解,数天磨难后,那一小块肌肤又平滑如初。于是,我决定顶着耳鸣照常上班。与同事对话,我好像漂流在海浪之中,隔着汹涌的潮水,我费力辨别他们的声音,而我的每一次发声都能听到旋转的回声,会被自己的大声惊到,也看到同事们惊诧而狐疑的神情。晚上回家,经过热闹的街口,世界在我眼里不同寻常的热闹,我行走在浪潮中,远处摇晃着高楼和人群,抬头,高耸入云的大厦,周身璀璨的灯光,黑夜如白昼般耀眼,光影交错,炫目迷离,像电影里的蒙太奇,梦境里的花朵与叹息。
耳鸣呈越发恣意扩散之势,不止海潮,又如蝉鸣 ,如火车的轰隆声终日鸣响。再去询问“度娘”:长期劳累、睡眠不足,均可导致耳鸣,当然,也不排除身体其他疾病的暗示……我不再熬夜码字,早早睡下。耳鸣,暗示我不是一个彻底健康的人。
我终于决定去医院,坐在医生面前,生命的抉择权完全由医生判定,有一丝惶恐不安。女医生戴着淡蓝色的口罩,我看不清她的容貌。她拉过我的右耳,拿一只特制的小手电筒,朝里面照一照,蝉鸣声中传递出语气平静的天籁之音:“没大问题,以后注意保持耳道干燥。”医生转过身,在电脑上写道:耵聍凝聚,阻塞于右外耳道内,诊疗室处置。
我在诊疗室门口等待,从包里掏出一本辛波斯卡的诗集《黑色的歌》,这本诗集,断断续续读了好久。我翻到动人的诗句:“风弯折树干/花瓣从树梢洒落/太阳如此令人感动”……终于轮到我,我躺在铺着洁白床单的诊疗床上,床边有一台立式诊疗器械,医生抽出一根极细长的管子,一股强大气流吹进右耳,有点恐惧,有点疼痛,我本能地抬起右手,试图抵挡在我面前不断移动的长管。机器轰鸣,但我还是听清了医生的话:“别动,马上就好。”当一切安静下来,我看见床头一张白色餐巾纸上,有一小块黄色的水斑痕迹,医生告诉我,这是从我耳朵里抽出的。原来真是有水入耳!出了诊疗室,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在身体里弥漫,我在医院的长廊上跑来跑去。我听见人们对话的声音,带着笑意,变得清晰而响亮。
回去的路上,经过河边的芦苇丛,地面之上风平浪静,一片萧瑟,谁知道,芦苇在水中潜滋暗长,泥土深处,盘根错节的根系蜿蜒逶迤,酝酿着生命的风暴,如今呈燎原之势,席卷河岸,以葱茏翠绿的娇羞,带给河畔弥漫的诗意。此刻,听觉变得异常灵敏,我听到芦苇丛中蛙虫鸣唱,野鸭的翅膀划过水流;我听到风吹过苇叶,此起彼伏的绵长声音,如一片乐海,声威远大。河水东流,想起孟子的一句话,“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其实悲与喜都是人生的波澜,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地势,带一颗平常心,奔流不息,一路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