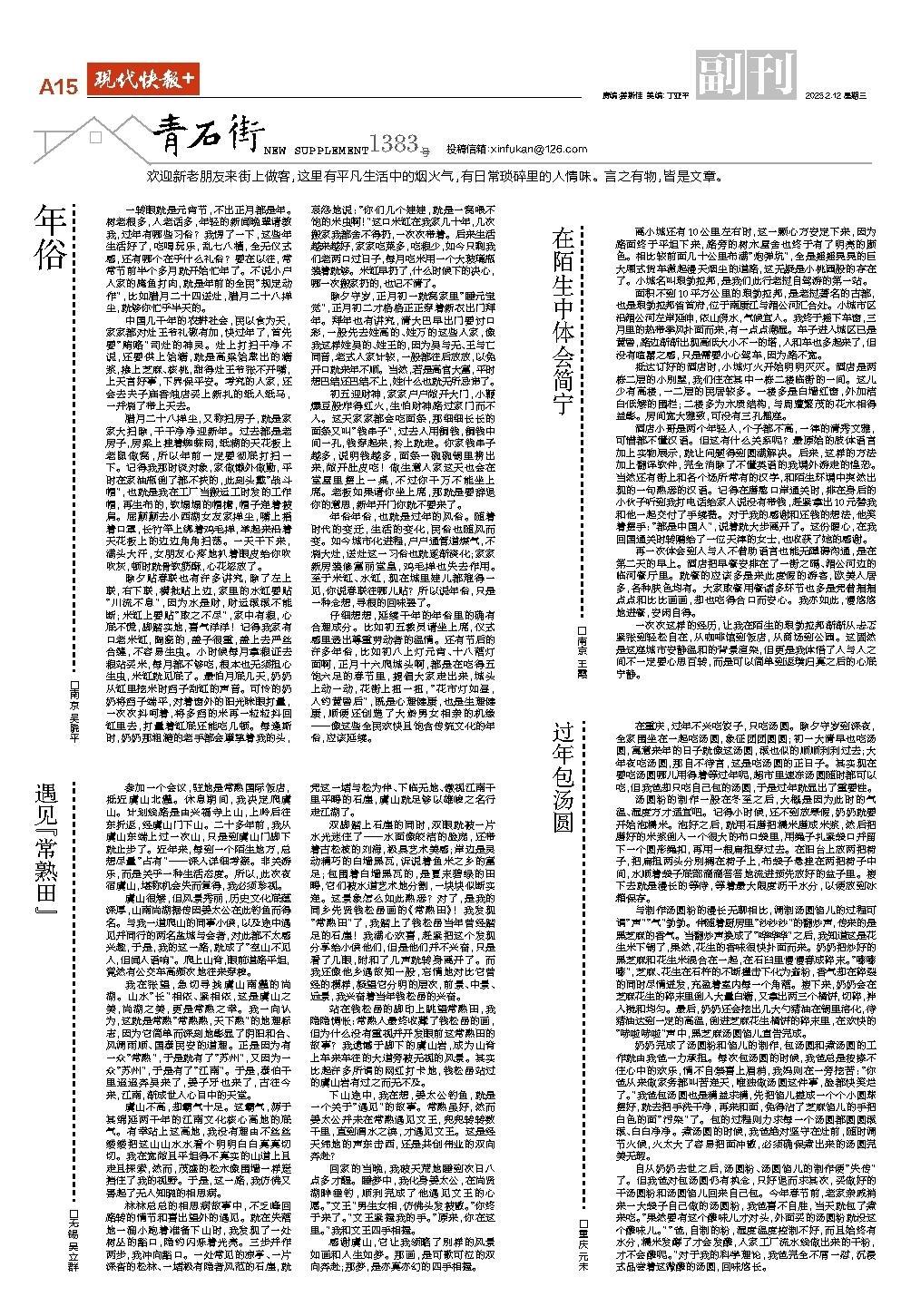□重庆 元未
在重庆,过年不兴吃饺子,只吃汤圆。除夕守岁到深夜,全家围坐在一起吃汤圆,象征团团圆圆;初一大清早也吃汤圆,寓意来年的日子就像这汤圆,滚也似的顺顺利利过去;大年夜吃汤圆,那自不待言,这是吃汤圆的正日子。其实现在要吃汤圆哪儿用得着等过年呢,超市里速冻汤圆随时都可以吃,但我爸却只吃自己包的汤圆,于是过年就显出了重要性。
汤圆粉的制作一般在冬至之后,大概是因为此时的气温、湿度方才适宜吧。记得小时候,还不到放寒假,奶奶就要开始泡糯米。泡好之后,就用石磨把糯米磨成米浆,然后把磨好的米浆倒入一个很大的布口袋里,用绳子扎紧袋口并留下一个圆形绳扣,再用一根扁担穿过去。在阳台上放两把椅子,把扁担两头分别搁在椅子上,布袋子悬挂在两把椅子中间,水顺着袋子底部滴滴答答地流进预先放好的盆子里。接下去就是漫长的等待,等着最大限度沥干水分,以便放到冰箱保存。
与制作汤圆粉的漫长无聊相比,调制汤圆馅儿的过程可谓“声”“气”勃勃。伴随着厨房里“沙沙沙”的翻炒声,传来的是黑芝麻的香气。当翻炒声换成了“哗哗哗”之后,我知道这是花生米下锅了,果然,花生的香味很快扑面而来。奶奶把炒好的黑芝麻和花生米混合在一起,在石臼里慢慢舂成碎末。“嘭嘭嘭”,芝麻、花生在石杵的不断撞击下化为齑粉,香气却在碎裂的同时尽情迸发,充盈着室内每一个角落。接下来,奶奶会在芝麻花生的碎末里倒入大量白糖,又拿出两三个橘饼,切碎,拌入搅和均匀。最后,奶奶还会挖出几大勺猪油在锅里溶化,待猪油达到一定的高温,倒进芝麻花生橘饼的碎末里,在欢快的“哧啦哧啦”声中,黑芝麻汤圆馅儿宣告完成。
奶奶完成了汤圆粉和馅儿的制作,包汤圆和煮汤圆的工作就由我爸一力承担。每次包汤圆的时候,我爸总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欢乐,情不自禁喜上眉梢,我妈则在一旁挖苦:“你爸从来做家务都叫苦连天,唯独做汤圆这件事,脸都快笑烂了。”我爸包汤圆也是精益求精,先把馅儿搓成一个个小圆球摆好,就去把手洗干净,再来和面,免得沾了芝麻馅儿的手把白色的面“污染”了。包的过程则力求每一个汤圆都圆圆滚滚、白白净净。煮汤圆的时候,我爸绝对坚守在灶前,随时调节火候,火太大了容易把面冲散,必须确保煮出来的汤圆完美无瑕。
自从奶奶去世之后,汤圆粉、汤圆馅儿的制作便“失传”了。但我爸对包汤圆仍有执念,只好退而求其次,买做好的干汤圆粉和汤圆馅儿回来自己包。今年春节前,老家亲戚捎来一大袋子自己做的汤圆粉,我爸喜不自胜,当天就包了煮来吃。“果然要有这个酸味儿才对头,外面买的汤圆粉就没这个酸味儿。”“爸,自制的粉,湿度温度控制不好,而且始终有水分,糯米发酵了才会发酸,人家工厂流水线做出来的干粉,才不会酸呢。”对于我的科学理论,我爸完全不屑一怼,沉浸式品尝着这微酸的汤圆,回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