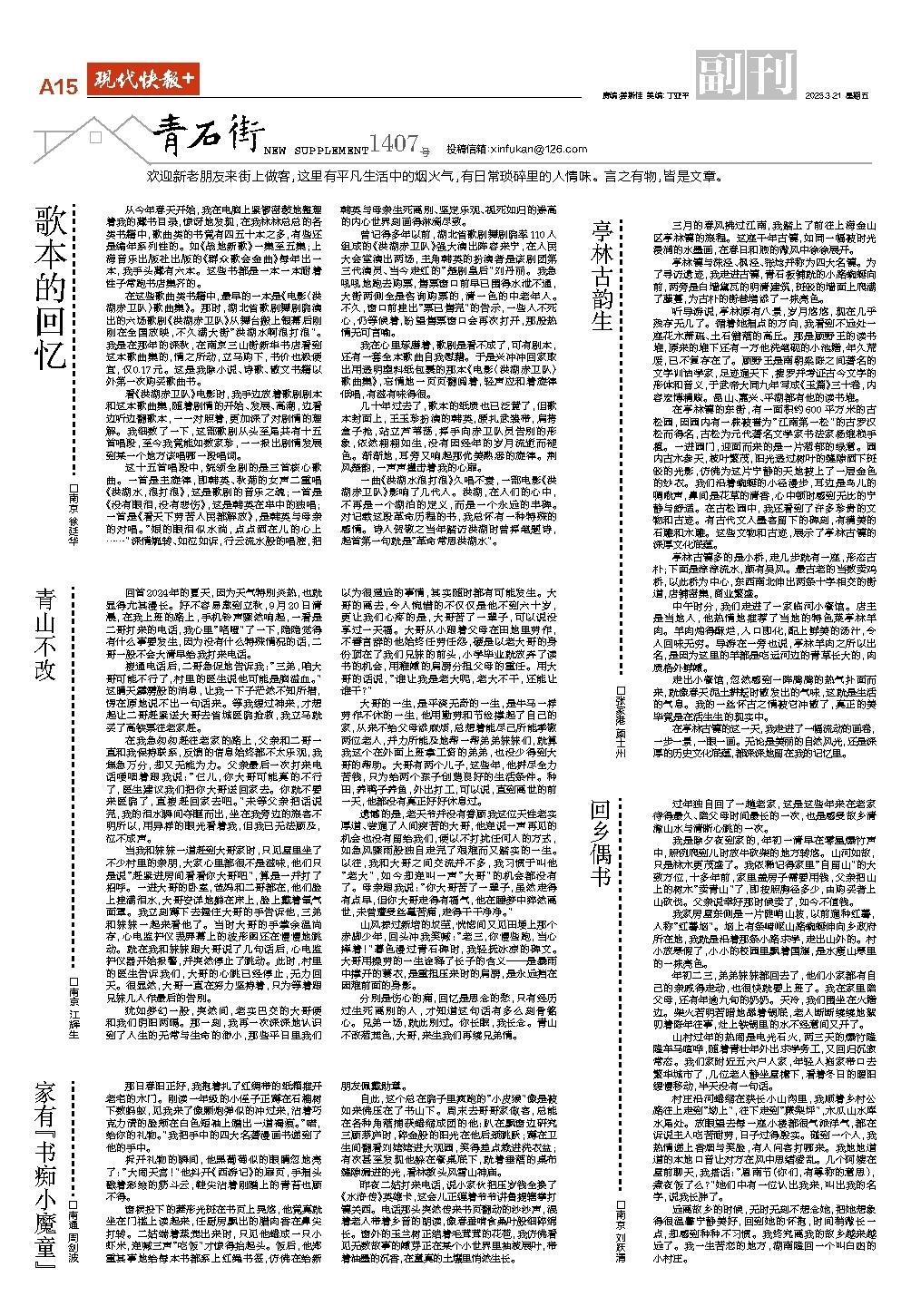□南京 刘跃清
过年独自回了一趟老家,这是这些年来在老家待得最久、陪父母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感受故乡清澈山水与清晰心跳的一次。
我是除夕夜到家的,年初一清早在零星爆竹声中,照例爬到儿时放牛砍柴的地方转悠。山河如故,只是林木更茂盛了。我依稀记得家里“自留山”的大致方位,十多年前,家里盖房子需要用钱,父亲把山上的树木“卖青山”了,即按照胸径多少,由购买者上山砍伐。父亲说幸好那时候卖了,如今不值钱。
我家房屋东侧是一片陡峭山坡,以前遍种红薯,人称“红薯垴”。垴上有条崎岖山路蜿蜒伸向乡政府所在地,我就是沿着那条小路求学,走出山外的。村小放寒假了,小小的校园里飘着国旗,是水瘦山寒里的一抹亮色。
年初二三,弟弟妹妹都回去了,他们小家都有自己的亲戚得走动,也很快就要上班了。我在家里陪父母,还有年逾九旬的奶奶。天冷,我们围坐在火塘边。柴火若明若暗地舔着锅底,老人断断续续地絮叨着陈年往事,灶上铁锅里的水不经意间又开了。
山村过年的热闹是电光石火,两三天的爆竹隆隆车马喧哗,随着青壮年外出求学务工,又回归沉寂常态。我们家附近五六户人家,年轻人拖家带口去繁华城市了,几位老人静坐屋檐下,看着冬日的暖阳缓慢移动,半天没有一句话。
村庄沿河蜷缩在狭长小山沟里,我顺着乡村公路往上走到“坳上”,往下走到“蕨梨坪”,木瓜山水库水尾处。放眼望去每一座小楼都很气派洋气,都在诉说主人吃苦耐劳,日子过得殷实。碰到一个人,我热情递上香烟与笑脸,有人问客打哪来。我地地道道的本地口音让对方在风中思绪凌乱。几个阿嫂在屋前聊天,我搭话:“恩南节(你们,有尊称的意思),煮夜饭了么?”她们中有一位认出我来,叫出我的名字,说我长胖了。
远离故乡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念她,把她想象得很温馨宁静美好,回到她的怀抱,时间稍微长一点,却感到种种不习惯。我终究离我的故乡越来越远了。我一生苦恋的地方,湖南隆回一个叫白凼的小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