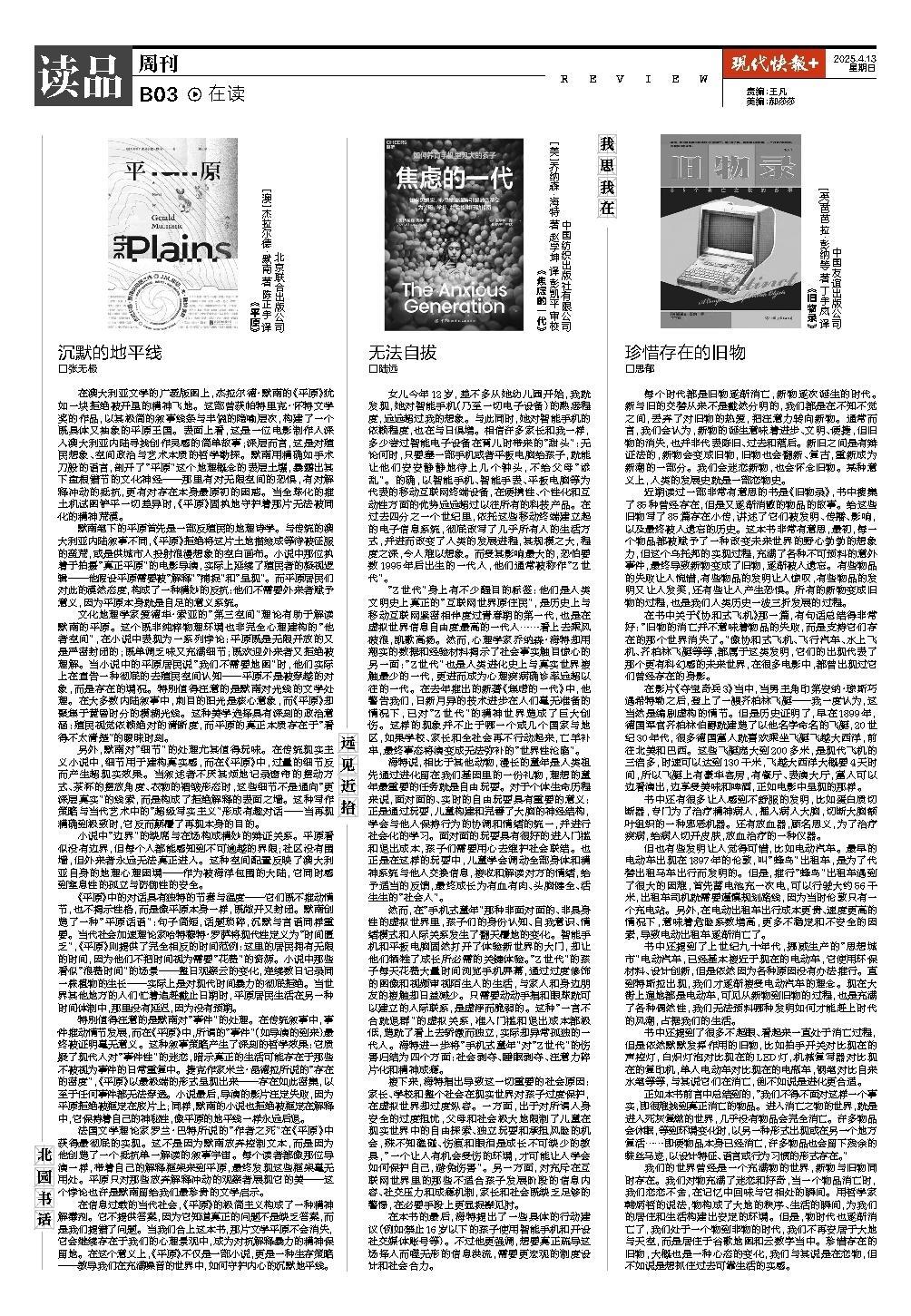□思郁
每个时代都是旧物逐渐消亡,新物逐次诞生的时代。新与旧的交替从来不是截然分明的,我们都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丢弃了对旧物的热爱,把注意力转向新物。通常而言,我们会认为,新物的诞生意味着进步、文明、便捷,但旧物的消失,也并非代表陈旧、过去和落后。新旧之间是有辩证法的,新物会变成旧物,旧物也会翻新、复古,重新成为新潮的一部分。我们会迷恋新物,也会怀念旧物。某种意义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恋物史。
近期读过一部非常有意思的书是《旧物录》,书中搜集了85种曾经存在,但是又逐渐消散的物品的故事。给这些旧物写了85篇存在小传,讲述了它们被发明、传播、影响,以及最终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本书非常有意思,最初,每一个物品都被赋予了一种改变未来世界的野心勃勃的想象力,但这个乌托邦的实现过程,充满了各种不可预料的意外事件,最终导致新物变成了旧物,逐渐被人遗忘。有些物品的失败让人惋惜,有些物品的发明让人惊叹,有些物品的发明又让人发笑,还有些让人产生恐惧。所有的新物变成旧物的过程,也是我们人类历史一波三折发展的过程。
在书中关于《协和式飞机》那一篇,有句话总结得非常好:“旧物的消亡并不意味着物品的失败,而是支持它们存在的那个世界消失了。”像协和式飞机、飞行汽车、水上飞机、齐柏林飞艇等等,都属于这类发明,它们的出现代表了那个更有科幻感的未来世界,在很多电影中,都曾出现过它们曾经存在的身影。
在影片《夺宝奇兵3》当中,当男主角印第安纳·琼斯巧遇希特勒之后,登上了一艘齐柏林飞艇——我一度认为,这当然是编剧虚构的情节。但是历史证明了,早在1899年,德国军官齐柏林伯爵就建造了以他名字命名的飞艇,20世纪30年代,很多德国富人就喜欢乘坐飞艇飞越大西洋,前往北美和巴西。这些飞艇庞大到200多米,是现代飞机的三倍多,时速可以达到130千米,飞越大西洋大概要4天时间,所以飞艇上有豪华客房,有餐厅、表演大厅,富人可以边看演出,边享受美味和啤酒,正如电影中呈现的那样。
书中还有很多让人感到不舒服的发明,比如蛋白质切断器,专门为了治疗精神病人,插入病人大脑,切断大脑额叶组织的一种邪恶机器。还有放血器,顾名思义,为了治疗疾病,给病人切开皮肤,放血治疗的一种仪器。
但也有些发明让人觉得可惜,比如电动汽车。最早的电动车出现在1897年的伦敦,叫“蜂鸟”出租车,是为了代替出租马车出行而发明的。但是,推行“蜂鸟”出租车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首先蓄电池充一次电,可以行驶大约56千米,出租车司机就需要谨慎规划路线,因为当时伦敦只有一个充电站。另外,在电动出租车出行成本更贵、速度更高的情况下,意味着危险系数增高,更多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素,导致电动出租车逐渐消亡了。
书中还提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挪威生产的“思想城市”电动汽车,已经基本接近于现在的电动车,它使用环保材料、设计创新,但是依然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办法推行。直到特斯拉出现,我们才逐渐接受电动汽车的理念。现在大街上遍地都是电动车,可见从新物到旧物的过程,也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我们无法预料哪种发明如何才能赶上时代的风潮,占据我们的生活。
书中还提到了很多不起眼、看起来一直处于消亡过程,但是依然默默发挥作用的旧物,比如拍手开关对比现在的声控灯,白炽灯泡对比现在的LED灯,机械复写器对比现在的复印机,单人电动车对比现在的电瓶车,钢笔对比自来水笔等等,与其说它们在消亡,倒不如说是进化更合适。
正如本书前言中总结到的,“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很难找到真正消亡的物品。进入消亡之物的世界,就是进入死灰复燃的世界,几乎没有物品会完全消亡。许多物品会休眠,等到环境变化时,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或在另一个地方复活……即便物品本身已经消亡,许多物品也会留下残余的蛛丝马迹,以设计特征、语言或行为习惯的形式存在。”
我们的世界曾经是一个充满物的世界,新物与旧物同时存在。我们对物充满了迷恋和好奇,当一个物品消亡时,我们恋恋不舍,在记忆中回味与它相处的瞬间。用哲学家韩炳哲的说法,物构成了大地的秩序、生活的瞬间,为我们的居住和生活构建出安定的环境。但是,物时代也逐渐消亡了,我们处于一个物到非物的时代,我们不再安居于大地与天空,而是居住于谷歌地图和云数字当中。珍惜存在的旧物,大概也是一种心态的变化,我们与其说是在恋物,但不如说是想抓住过去可靠生活的实感。